
《史上首個(gè)啥都不好使的大使》出續(xù)集了,導(dǎo)演還是周寧寧。
據(jù)說看到腳本的第一眼,他就嗨了:“太絕了,這就是我想要的idea。”
后續(xù)的勘景、拍攝、后期一條龍,像打了興奮劑一樣快速推進(jìn)。
項(xiàng)目還沒出街時(shí),他就言之鑿鑿:你們肯定會(huì)喜歡,李雪琴搭向佐,這組合絕了!
片子出來后,果然,評(píng)論區(qū)全是樂得合不攏嘴的“哈哈哈”。
輕松、愉快的觀看體驗(yàn),反轉(zhuǎn)再反轉(zhuǎn)的劇情展開,延續(xù)著第一支的主題和基調(diào),也是周寧寧最為人熟知的影像風(fēng)格。
等等,周寧寧是誰?
或許是“寧寧”太過親昵可愛,而他又1米8幾的大高個(gè),熟悉他的人也叫他周寧。
在這幾年的熱門廣告作品中,大家與他早已熟識(shí):
從美團(tuán)《像哥一樣享受春天》《美團(tuán)六一:有些快樂,大人特供!》《小象超市:會(huì)長(zhǎng)大的家》《胡歌歌歌歌歌歌歌》;
或者,海飛絲《去屑護(hù)頭皮當(dāng)然海飛絲》《看不見的禮物》;
再或者,大眾點(diǎn)評(píng)兩支接連出圈的《史上首個(gè)不好使的大使》《不好使的大使增加了》......

品質(zhì)和數(shù)量齊頭并進(jìn),周寧寧迎來了作為廣告導(dǎo)演的“收獲的季節(jié)”。
掀起口碑和名氣的聲浪,周寧寧也成了值得討論和關(guān)注人物。外界常常用接地氣、幽默形容其作品風(fēng)格;用“時(shí)間管理大師”評(píng)價(jià)其工作狀態(tài)。
對(duì)于不請(qǐng)自來的標(biāo)簽,他很不適應(yīng),也不太敢接受:
“喜劇太難做了,我不敢說自己拍的是幽默類型片,相較于整個(gè)市場(chǎng),我拍的只是更廣告感的廣告片。
我只是希望大家看的時(shí)候輕松點(diǎn),所以總?cè)滩蛔》劈c(diǎn)輕松的東西進(jìn)去。
另外,花橋小田切讓,走顏系的,不接地氣。謝謝。”
周寧寧覺得,這里面有誤會(huì)。
于是,我們問他:
數(shù)英:“那你覺得自己是什么風(fēng)格?”
周寧寧:“廣告導(dǎo)演應(yīng)該有風(fēng)格嗎?”
數(shù)英:“你覺得你拍的是什么?”
周寧寧:“人,普普通通的人。”
數(shù)英:“可你拍了很多明星。”
周寧寧:“都是人,鮮活真實(shí)的人。”
以下是周寧寧的自述——
01
只有拍人才能讓我興奮起來
只有拍人才能讓我興奮起來。
人,是我最重要的拍攝主題,我拍過很多普通演員,素人,明星。
我是靠演員活著的導(dǎo)演。我在挑選演員時(shí)會(huì)盯著他們的眼睛看。
我覺得廣告片里的角色,不管是主是配,都應(yīng)該是有趣的立體的。有時(shí)候,一個(gè)十五秒的tvc我也會(huì)忍不住給角色寫個(gè)人物小傳。
對(duì)于素人演員,我給casting的要求永遠(yuǎn)是:有趣的素人感。
解釋一下就是:觀眾會(huì)想和這個(gè)人交朋友,和他(她)一起吃飯聊天。喜歡他(她),愛上他(她)。
好演員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有段時(shí)間,我特別想把我覺得好的演員拍火,想拍火“我自己的演員”,既以此證明自己的能力,也想幫助他們生活得更好。
《大人的兒童節(jié)》里的一個(gè)男孩原來只是特邀,拍完那支廣告后變得特別搶手。
我特別有成就感,當(dāng)然也因?yàn)樗约簤蚺Γ心芰ΑN矣X得,導(dǎo)演就應(yīng)該像一棵大樹,給周圍人提供空間和養(yǎng)分。


這兩年刮起的一股新的藝人廣告風(fēng)在成就我。我拍的很多藝人廣告里,東北明星占大半。
有時(shí)候,制片一看是東北藝人,就會(huì)遞本子。他們開玩笑說:一看腳本和人選,就覺得腳本上寫著你名字。
誰能想到,廣告導(dǎo)演竟然也能吃上籍貫的紅利。這都要感謝東北文藝復(fù)興,東三省文體兩開花,以及東北話的神奇魔力。
東北人天生就有讓對(duì)話變得好玩的天賦,我也喜歡自己寫臺(tái)詞。
我拍過很多次賈冰,每一次給他寫的臺(tái)詞他演起來都特別流暢;雪琴的廣告片下面的評(píng)論也都說是雪琴自己寫的腳本吧;和喬杉合作時(shí)見面就用他十幾年前的名字梗迅速拉近了距離......
人物臺(tái)詞不是單純的廣告詞。人們都是得先接受了這個(gè)人,才能接受他承載的商業(yè)屬性。
所以,廣告文本變成人物語言也必須得貼合人物,要足夠生活化。
順便說一句,我一直覺得最好的演員才會(huì)演喜劇。他們必須得是非常聰明的一群人,才能把這事做好。因?yàn)椋屓诵?shí)在太難了。
這股新的拍藝人的風(fēng)格在成就我,我也在或多或少地回饋這股風(fēng)潮。
我不覺得自己算什么標(biāo)桿,更不敢標(biāo)榜有能力引領(lǐng)趨勢(shì)。但我們的確在提供更多樣本,就和其他兢兢業(yè)業(yè)的廣告導(dǎo)演一樣。
很多人評(píng)價(jià),“同一個(gè)藝人,我拍出來的總會(huì)奇奇怪怪的”。對(duì)此,我感到很驕傲。
以前的藝人廣告太限制在模式化里,我總想方設(shè)法讓他們更鮮活一點(diǎn),有反差感一點(diǎn)。
所以我拍的劉德華變成了產(chǎn)品的配角,姚安娜玩起了自己名字的諧音梗,時(shí)代少年團(tuán)變成了旅行團(tuán)……結(jié)果大家都還挺喜歡的。


這種趨勢(shì)國外早就有了,比如《TAYLOR vs. TREADMILL》里的泰勒就摔了個(gè)大馬趴。
很鮮活,很自然,又有趣味的化學(xué)反應(yīng),這是用藝人的最高境界。
我們現(xiàn)在也在朝著這個(gè)方向前進(jìn)。
品牌在拓展更多可能性的藝人與自己進(jìn)行合作,創(chuàng)意們跳脫過去的套路化讓藝人有血有肉,藝人本身也越來越玩得開,廣告導(dǎo)演們更應(yīng)該多去挖掘藝人表演形態(tài)的多面性。
這不是一個(gè)人、一個(gè)職業(yè)能帶來的改變,是所有人都在讓廣告變得更好。
02
被貼標(biāo)簽的感覺,幸福又痛苦
我喜歡輕松+愉快的東西,希望觀眾在我的片子中獲得精神上的休息。
因此,每次拍片時(shí),我總?cè)滩蛔〖右恍┹p松的元素。這可能是東北人的天性吧。
我不喜歡把片子弄得太厚重太復(fù)雜。
我總愛做減法,把那些對(duì)idea沒幫助的元素剔除掉。
我總覺得,觀眾就給了我這么一點(diǎn)兒時(shí)間,我能給他們講清楚一件事兒就不錯(cuò)了。
有時(shí)候我跟主創(chuàng)們開玩笑說,我像是廣告圈里的王晶。我拍的廣告沒什么藝術(shù)性,也不夠深刻,看的時(shí)候沒壓力,看完也不好意思說喜歡。
但我想證明:有趣的廣告也可以有效,有效的廣告也可以好看。大眾點(diǎn)評(píng)一年增加一個(gè)億的用戶量就是證據(jù)。

由于這種創(chuàng)作習(xí)慣和審美偏好,加上這幾年拍了很多喜劇藝人,很多人覺得我是專拍幽默廣告的。
被貼上標(biāo)簽的感覺,既幸福又痛苦。
以前的監(jiān)制對(duì)我說:“你不太好賣,因?yàn)槟闶裁搭愋投荚谂模糠N類型里,第一個(gè)想到的都不是你。”
如今能被貼標(biāo)簽,說明情況在改變,至少在幽默廣告這個(gè)領(lǐng)域里,我被人想到了。
不過,我也特別警惕,可以說是如履薄冰。害怕自己被定性在一種風(fēng)格里。
我非常佩服李靜波、林哲樂這些成名已久的導(dǎo)演,他們依然還在探索新的視聽語言和表達(dá)方式。
所以,我和主創(chuàng)們每條片都要商量,這次怎么可以不一樣。怎么和別人不一樣,怎么和自己不一樣。

廣告這個(gè)東西,存在的周期挺短的,但反映著流潮甚至引領(lǐng)著潮流,是對(duì)審美提升幫助最大的。
一張海報(bào)的排版、一句戶外的文案、一支廣告片……那些每天出現(xiàn)在各個(gè)地方的廣告都在潛移默化地產(chǎn)生影響,帶來改變。
作為從業(yè)者,在自我風(fēng)格、社會(huì)審美上再多探索點(diǎn)兒就顯得更重要了。
以前,別人問我“為什么堅(jiān)持留在廣告界”,我的回答是:想為提升下一代的審美做貢獻(xiàn)。
我并沒有帶著什么偉大的使命感去看待我的工作,但我既然擁有這樣的可能性,我就不想把它讓給那些低劣的、洗腦的、丑陋的廣告。
我希望,每個(gè)孩子在電梯里看到的,都是有趣又好看的廣告。

03
廣告導(dǎo)演的職責(zé)是保護(hù)idea
Idea,對(duì)我來是最最寶貴的東西。消費(fèi)者洞察在任何時(shí)代都會(huì)被需要。
產(chǎn)品是戲劇的轉(zhuǎn)折,是推動(dòng)故事發(fā)展的驅(qū)動(dòng)力。一支好的廣告片就像一個(gè)謎題會(huì)吸引著你一直看下去,只有加上產(chǎn)品才會(huì)知道謎底。
我覺得廣告導(dǎo)演不該抗拒品牌和產(chǎn)品,廣告片畢竟不是我們的個(gè)人表達(dá)。
一個(gè)正常的廣告片就是應(yīng)該以產(chǎn)品和品牌為骨架,而不是表面的,鑲嵌上去的,生拉硬拽的。產(chǎn)品是腳本邏輯的閉環(huán)。如果在一個(gè)廣告片里產(chǎn)品沒有角色,那我過不了我自己這關(guān)。

廣告片的制作流程是一個(gè)接力賽,好idea本身就是合作質(zhì)量、成片質(zhì)量的基本保證。
一個(gè)優(yōu)秀的腳本后面是一群非常聰明的創(chuàng)意在產(chǎn)出idea,一群非常聰明的客戶在做決策,廣告導(dǎo)演和制作團(tuán)隊(duì)只能決定這條片的底限,創(chuàng)意腳本才是品質(zhì)的上限。我們要做的就是控制自我感動(dòng),不要把這個(gè)idea搞砸了。
保護(hù)idea,是廣告導(dǎo)演的天職。
一個(gè)腳本的誕生很難,現(xiàn)在的大環(huán)境下,甲乙方推進(jìn)一個(gè)項(xiàng)目不容易,持續(xù)真心實(shí)意投入的人也是非常可貴。所以每次接到腳本,我都會(huì)先找到那個(gè)idea,然后重點(diǎn)保護(hù)它。
創(chuàng)意和客戶又都會(huì)有自己的喜好和期待想塞進(jìn)去。我覺得這不是壞事,至少說明大家都為這個(gè)腳本投入了感情。所以,我都會(huì)盡量想辦法滿足這些要求,當(dāng)然有時(shí)候也是罵罵咧咧地想辦法。

你們問我,“廣告導(dǎo)演是不是討好的角色?”我對(duì)此不太有發(fā)言權(quán)。但是從這件事上來說,我的確有點(diǎn)取悅型人格。
我總給自己催眠說一定會(huì)有一個(gè)辦法可以滿足所有要求,讓所有人開心,只要給我一點(diǎn)空間,不用太多,一點(diǎn)就夠了。
星巴克圣誕節(jié)那支廣告,原本的腳本是費(fèi)翔靈機(jī)一動(dòng)做了一個(gè)很好的咖啡拉花。
我跟客戶說我想改一點(diǎn),變成了費(fèi)翔不會(huì)做,原來是店員做的。
一個(gè)很小的變動(dòng),片子就有了趣味小反轉(zhuǎn),藝人不再套路化的高大全,品牌凸顯了專業(yè)性,店員也能和明星互動(dòng)。客戶和創(chuàng)意都很開心。
我從“夾縫”中找到了轉(zhuǎn)身的空間,讓idea表達(dá)得更充分,也讓各個(gè)角色都心滿意足。我覺得這就是取悅了所有人。
在呈現(xiàn)idea上,有的導(dǎo)演喜歡“增色添彩”,我喜歡“打磨拋光”,做減法。
越優(yōu)質(zhì)的食材越需要簡(jiǎn)單的烹飪方式。我不希望有多余的東西干擾idea,只要故事合理、人物立得住,對(duì)話符合情境,這條片看起來就會(huì)很流暢。
所有的形式為內(nèi)容服務(wù)。保留下來的元素只是為了建立起一個(gè)idea。
《大人的兒童節(jié)》的創(chuàng)意腳本洞察本身就很精準(zhǔn)了,原本腳本里也有一些額外的表演,比如擠眉弄眼地氣那些孩子。我把這兩個(gè)男主的反應(yīng)全部冷處理。這看起來是很小的點(diǎn),但事實(shí)上,“氣孩子”的行為里是有攻擊性的,就會(huì)讓這兩個(gè)男生不可愛了。
這個(gè)處理的核心原因是因?yàn)槲乙恢倍疾挥X得小孩就比大人更幸福,我覺得應(yīng)該先讓觀眾同情他們。
小孩就那么點(diǎn)高,看到的永遠(yuǎn)都是別人的屁股,想吃什么喝什么都得看大人臉色,幾乎沒什么自主權(quán)。小孩和大人都有自己的苦惱,表演出對(duì)立感是完全沒必要的,對(duì)idea的表達(dá)也有害。效果反饋?zhàn)C明這種思路正確。


不只是畫面,給文本做減法也很重要。導(dǎo)演需要有一定的文本意識(shí)和權(quán)利。
我給彩虹糖拍廣告的時(shí)候,品牌global的老大直接跟我說“彩虹糖的廣告不能讓所有人都看懂,要往里面加 30% 讓人看不懂的東西。懂又不全懂。”
意思是人琢磨出來的,講太明白就沒意思了。有時(shí)候話也不需要說那么白,說那么多。留給觀眾一些自我思考的空間,從思考中獲得樂趣。
當(dāng)然,有時(shí)候我刪減掉的字也只是因?yàn)?5秒的時(shí)長(zhǎng)真的塞不進(jìn)17秒的對(duì)白。
04
因?yàn)樽銐螂y,才更值得去做
這幾年,行業(yè)變得更卷,每個(gè)廣告人都能切身會(huì)到生存環(huán)境的愈加嚴(yán)峻。
不嘮經(jīng)濟(jì)大環(huán)境的原因,行業(yè)內(nèi)部的亂象是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國外也經(jīng)歷過秩序重建的疼痛,最后,從混沌中生長(zhǎng)出了規(guī)則。
行業(yè)有自己的糾錯(cuò)體系,總會(huì)彎彎繞繞地前進(jìn)。我們要做的就是一起努力活下去。
大家都活著,才會(huì)有希望;大家都好,行業(yè)才會(huì)好起來。
行業(yè)的良性生存就更需要靠?jī)?yōu)秀的作品、優(yōu)秀的人來拉動(dòng)。
因?yàn)榭蛻艨倳?huì)向出圈的好作品看齊,只要大家把更多精力放在打磨腳本上,產(chǎn)出好作品的成本就會(huì)更可控。
拍片是我的興趣所在,也是我汲取養(yǎng)分的過程。我常說“我是為廣告而生的人。”
這聽起來賊裝逼,但我想表達(dá)的意思是:
我有點(diǎn)笨,其他事都做不太好,索性就把僅有的這點(diǎn)兒智慧劃拉劃拉集中到一點(diǎn)了,就專心拍廣告了。
我看到好的idea就會(huì)興奮,拿到喜歡的腳本的一瞬間,表演、分鏡、節(jié)奏、畫面自然就在腦袋里出現(xiàn)了。
我也沒有覺得累,拍片、出現(xiàn)場(chǎng)對(duì)我來說才像度假,像和好朋友們一起去春游。
能把自己唯一擅長(zhǎng)的事情變成職業(yè),已經(jīng)非常幸運(yùn)了,我還有什么理由不all in。

從開始做廣告到現(xiàn)在,我一直都想拿“獅子”。
現(xiàn)在更是想如果能以導(dǎo)演身份拿到個(gè)獅子該多好。
雖然這幾年,大家對(duì)戛納態(tài)度挺微妙的,但我覺得中國廣告不應(yīng)該與世界脫軌。
那種不需要懂語言也可以看懂看笑看哭的創(chuàng)意永遠(yuǎn)是我們追求的目標(biāo)。
前幾天,我剛參加完戛納,這次仍止步入圍,但是也沒什么可灰心的。有些事,正是因?yàn)樽銐螂y,所以才更有意思,更值得去做。
周寧寧2024戛納入圍短片《早上海》
人類文明是基本同步的,洞察是全人類皆準(zhǔn)的。
我和木瓜創(chuàng)意合作的小象超市《會(huì)長(zhǎng)大的家》,它的對(duì)白很少,故事很簡(jiǎn)單,但是所有觀眾都是能看懂的。它的語言是國際化的。
當(dāng)我們把原本房子自動(dòng)變大的設(shè)定調(diào)整成兩個(gè)人要努力地推動(dòng)墻壁讓房子變大,它就把洞察視覺化了。觀眾可以從中看到為一個(gè)家拼命奮斗的自己。
這種調(diào)整是有價(jià)值的,超越了語言的限制。我相信這樣的表達(dá)是能被全世界人民接收到的。我就想做這樣的廣告。
采訪后記:
當(dāng)我們邀請(qǐng)周寧寧接受訪談時(shí),他戲稱自己講話太直接,說得沒有其他導(dǎo)演的深刻又好看。
但一旦話鋒轉(zhuǎn)向創(chuàng)意和拍片,他又是一副自信開朗的模樣。
時(shí)間的分量忽輕忽重,切換出飽滿和沉靜兩種狀態(tài),生命的彈性便開始釋放,翻涌起褶皺和光華。

周寧寧的人生,就像他的作品,充滿了反轉(zhuǎn)和戲劇性。他總會(huì)強(qiáng)調(diào):
我其實(shí)是一個(gè)特別膽小、內(nèi)向的人,怕惹麻煩、怕做改變。
但是,轉(zhuǎn)行做廣告導(dǎo)演,包括離開家鄉(xiāng),做北漂,滬漂,人生中很多重大的決定,懵懵懂懂地就做了。如今回頭再看,這些好像早就寫好了,特別宿命。”
命運(yùn)只給予我們一種選擇,冷眼旁觀我們苦尋自己的那條路,不予以任何暗示。
就如周寧寧所說,“人生也是猜謎,選擇的時(shí)候全靠蒙。”
但也正因如此,它才足夠好玩。喜惡、原則、風(fēng)格、野心......那些堅(jiān)持才更有意義,須得始終報(bào)以努力、智慧、勇氣一往無前,就如同周寧寧說的:
“人生也是猜謎,選擇的時(shí)候全靠蒙。
但是只要懷著敬畏之心做好當(dāng)下,那么所有的安排,即是最好的安排。”
轉(zhuǎn)載請(qǐng)?jiān)谖恼麻_頭和結(jié)尾顯眼處標(biāo)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未經(jīng)授權(quán)嚴(yán)禁轉(zhuǎn)載,授權(quán)事宜請(qǐng)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quán)必究。
本文禁止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授權(quán)事宜請(qǐng)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hào)(ID: digitaling) 后臺(tái)授權(quán),侵權(quán)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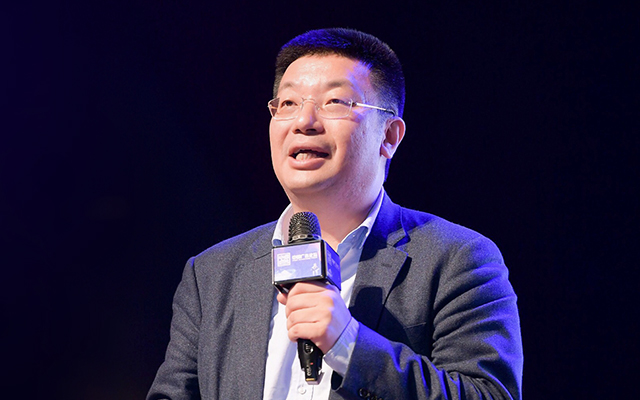




評(píng)論
評(píng)論
推薦評(píng)論
全部評(píng)論(6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