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新媒體的人,最后都變得怎樣了?
原標題:《老子再也不想干新媒體了!》
來源:娛樂產業
也許是身在此山中的緣故,娛sir一直感覺新媒體從業者跳槽、轉行的頻率遠超旁人,往往是昨日剛交換了新公司的名片,今天就施施然地說要退出江湖、另覓出路了。而此次的“寒冬”反而像是刺激了大家轉行的熱情,娛sir身邊的朋友一個個好像下餃子,噼里啪啦四散開去了。
而近來,我們又見過太多CEO 、創始人對著媒體哭訴“寒冬”了,他們一個個哭得梨花帶雨,悠揚婉轉,手舞足蹈。真可謂我見猶憐,恨不得在公益平臺上發起眾籌,不讓他們的眼淚陪他們過夜。
食君之祿,為君分憂,為了讓老板們故事的戲劇沖突更加明顯,讓大家真的去公益平臺給他們眾籌過冬,我們特此策劃本期選題,從自己的同行下手,找了五位新媒體老師來聊聊的他們的從業感慨。
他們不是已經轉了行,就是在轉行的邊緣試探。而他們所袒露的種種心緒,若是同行看到后,能產生一份共鳴,少一份孤獨,就是對我們最大的褒獎。
本文立場不客觀、取樣不全面、素材不友好,唯一能保證的,是它就像新媒體行業一樣靠譜。
1、
ID:哭泣的小山由
星座:水瓶
新媒體方向:娛樂
“我們組內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遇上迪麗熱巴就往死里夸。”
在一個不算寒冷的冬天我踏上了北漂之路,走向了新媒體行業的不歸路。
說起我的北漂之旅,真是深刻貫徹了漂這個字的所有負面色彩,住的地方是一屋子六個人的青年旅館,以前我以為自己的宿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后來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不過一彈丸之地集結了天難海北的過客,有想整容團購做鼻子的,有身患重病前來治療的,有前一秒還灰頭土臉下一秒就辦簽證準備出國的,形形色色的人來來往往,那些在半夜熄燈之后還打電話的永遠都會成為人民公敵被釘在恥辱柱上。
我很討厭待在住處,所以很期待上班的日子,埋頭苦干比什么都實在,它可以完全占據你用來胡思亂想的時間,一個成熟的新媒體從業者,應該像我一樣寵辱不驚安心碼字,在娛樂的浪潮里做一條一天到晚游泳的魚,自在而又飄逸,不過我這條魚,沒蹦噠多久就死在了沙灘上。
第一個拍暈我的浪花是頂級流量迪麗熱巴,當初我們自己微薄靠著吹迪麗熱巴賺足了她粉絲的好感狠狠圈了一波粉,于是在我們組內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遇上迪麗熱巴就往死里夸。
當時我的選題是迪麗熱巴的新劇《烈火如歌》,主編給我下了死令不準批評熱巴一句,于是那一天我無視豆瓣如海的吐槽把迪麗熱巴繃緊發際線露出大腦門的造型愣是夸成俏皮可愛少女感滿滿,那一天我憋出了嚴重的內傷,靠著下單買了一件心水很久的襯衫才勉強回魂。

第二個的拍暈我的浪花是一部小成本偶像劇,它是一部腐劇,放在平時也沒有什么,偏偏在我嘔心瀝血碼完一篇純愛之作良心推薦文之后,公司下了一份文件,說同性戀是敏感詞匯,杜絕該類稿件出現,于是當天我操刀把一段愛情故事生生掰成了兄弟情,內傷過重的我對著電腦就是一口老濁血。
什么緊跟時代潮流,充分發揚創作自由都是騙鬼的,這一切都是新媒體行業的自欺欺人,很多像我一樣的新媒體小編頂著評論區罵聲一片卻根本無處申冤,老子再也不想干什么新媒體了!
沒過多久我就收拾行李離開了那個傷心之地,后來我也時常想起自己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想起自己每天早上擠在沙丁魚罐頭一樣的地鐵里握著手機怕被人偷走,在那個城市人始終沒有歸屬感,也沒有快樂可言,但是這個擁擠的城市卻始終以它獨特的魅力吸引著許多人去到哪里,它的發達它的繁華,后來很久很久都是我夢境里的主要畫面。
2、
ID:不做大哥好多年
星座:天蝎
新媒體方向:代運營
“我一個科班出身的,現在做這個,跌份啊!”
大學學的新聞專業,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我們組拍的紀錄片放完了之后 ,老師說,大家都自發鼓掌了,證明這個紀錄片就是觸動到大家的了。
畢業后做的新媒體代運營,印象最深的,是甲方的一個字:“發”。
我一個科班出身的,現在做這個,跌份啊。
感覺甲方是扶不起的阿斗 ,每天都要被氣死,要增粉要閱讀量,結果想出來的好策劃一個不愿意做,做了活動不愿意出錢,拉贊助還不愿意溝通 。
你見過發給你文檔之后,讓你給他打電話(劃重點:他不愿意打過來) ,然后把文檔給你讀一遍,最后問你懂了嗎的人嗎?然后,遠程問你你看到哪哪哪了嗎,回答嗯嗯看到了,然后他說那你讀一遍我說的范圍——這不是我,是我同事的經歷哈哈哈哈哈。
還有甲方說,我想要歐式風格一點的排版,全辦公室爆笑。

因為甲方,現在我覺得辛苦了三個字和對不起一樣沒用。
做新媒體感覺把我自己打碎了,讓自己不嚴謹了,現在做新媒體,因為要活潑,要新穎,會在文章中加隔斷,比如以小編的話插幾句話,用表情包帶動一下情緒——可能是在下矯情了。
工作最觸動我的點在最近一篇稿子,我那個老師讓我們學習一下某日報的稿子,看完之后發現那種稿子就是在學校里老師讓我們練習寫的稿子啊 。
所以新媒體和我想象中做新聞不一樣,做新聞就是要跑出去啊,我們一位老師是從十年傳統媒體下來的,她說她以前就是到處跑,我只是在當搬運工,并沒有自己出去采編。
現在有想自己平時寫寫東西,有一些工作經驗之后再去傳統媒體試試(感覺自己反著方向走,大家都是傳統媒體到新媒體。我從新媒體到傳統媒體)。所以我會努力早日走向傳統媒體!擁有采編資格!
老板太多槽點了,但是我不敢說。我覺得他太奇葩了,應該沒幾個跟他一樣,我說出來可能就暴露了。
3、
ID:林秀樹
星座:處女
新媒體方向:科技新媒體
“人不寐,媒體民工社畜淚。”
如果不做新媒體,我可能會成為一名三流甚至四流編劇。
我大學專業叫戲劇影視文學,有時候跟非業內人士聊天,人家會試探性地問一句,“那就是中文系吧”?臉上帶著七分肯定,兩分疑惑,一分不可說。
久而久之,我一般說,我的專業就是寫劇本,對對對比如網大那種。什么《校花與野出租》啦,《盲少爺戀上我》啦,《校花駕到之極品佳人》啦。
好啦,今年網大也不行了。曾經心比天高的我和我的同學們,有去當幼兒園老師的、有做微商的、有去報社跑民生新聞的、有創業賣榴蓮酥的、有進廣告公司的、有當家庭主婦的,還有像我這樣搞新媒體的。
那么,新媒體的前景怎么樣呢?去年,我爸他妹妹的大女兒在高考志愿填報的前三天問了我這個問題。本著“再坑不能坑親戚,再窮不能窮教育”的原則,我送給了我爸他妹妹的大女兒一句話——“人不寐,媒體民工社畜淚。”

自從成為了一名光榮的新媒體工作者,熬夜成了我的特長,蹭熱點成了我的墓志銘,我的本體徹底淪為人型打字機。我不是在熬夜趕稿,就是在熬夜趕稿的路上。遇到一些熱點,蹭吧,太沒節操了,不蹭吧,第二天閱讀量分分鐘教你做人。
此時此刻,想起小崔還沒瘋魔前的那句,“收視率是萬惡之源”。
如果只是累點辛苦點錢拿得少一點,我覺得新媒體工作還能忍受。畢竟老本行里,拖欠編劇稿費的操蛋事兒也是一籮筐。我對新媒體工作最大的不滿在于,這個行業為了追求閱讀量的好看,有時候是看不到底線在哪兒的。
沒有底線,所以可以洗稿,可以刷閱讀量,可以吃人血饅頭,可以在同行由于某些原因被404時洋洋自得地說活該。我覺得這樣很難看,大環境艱難至此,為什么還要互相傷害呢?
我覺得在當下的新媒體業內,流量有時候不再是對優秀創作者的獎賞,而變成了一種詛咒,大家在探索如何獲取流量的過程中,已經不知不覺地背叛了一些東西,比如理性、邏輯、誠實。什么出格寫什么,怎么煽動情緒怎么寫,比網大還會戳讀者G點。
我這樣說好像也不對,畢竟“要吃飯的嘛”。于是在去年,影視業寒冬還沒來臨前的那個高考后的夏天,我對我爸爸他妹妹的大女兒說道,
“搞新媒體工資很低,我建議你報編導。”
4、
ID:歡脫的菜菜
星座:水瓶
新媒體方向:TMT與泛娛樂
“新媒體讓我成為我最討厭的樣子。”
直到今天,我媽都會和我說,兒啊,你可真優秀,能在北京找到工作混下去,你看我們公司老李/老張/淑芬/他兒子......
每到此時,我都想臥冰求鯉一下,證明自己孝感動天,最后順勢一跪,娘親,孩兒不孝,只能讓你精神勝利了。貴司老李家的公子,靠著當年在北京學到的老北京章魚小丸子,都買奧迪A6了。
而我,還是一只糾結本月花唄要不要最低還款的,公號狗。
但錢不是問題,畢竟我長得就不像能開奧迪A6的少爺,吃得起西少爺肉夾饃已經讓我感恩公司了。平心而論,我先后做事的幾家新媒體都是業界比較不錯的,但俗氣地說,這些經歷仍然讓我不可逆地滑向曾經最討厭的樣子。
常常恐懼地發現,現在會不自覺地使用一些“技巧”,“不動聲色”地挑逗讀者的情緒點,內心戲如我,常常帶著壯士斷腕的悲壯感刪去它們,獲得一種近乎自虐的快感——通過規避更好看的轉發閱讀數據,來實現一次意淫,仿佛一個腦袋后面帶光圈的老頭笑瞇瞇地拍拍我的肩膀:你干得真不錯。

大概就像這樣
難以抑制的還有戾氣,曾經真誠地認為寫作者和讀者是平等的,我要向讀者謙虛請教;現在則真誠地篤信,腦子和腦子的鴻溝是難以跨越的,智商降級是大勢所趨的,而能看到我稿子,是大多數讀者三生有幸的——剛入行的時候,幾個關系好的同行私下里,吐槽說一些媒體前輩還是安靜地寫稿子吧,不要在社交平臺上暴露自己的傲慢狹隘無趣淺薄了,現如今自己這股自鳴得意的勁,自己看了都尷尬癌爆表。
所以下份工作一定不會做新媒體了,不想賦予自己唐吉柯德式的戲碼。
說來尷尬,現如今覺得最值得尊重的自媒體人反而是咪蒙老師,人家想要流量直接說,坦蕩率直,敢做敢當;反觀很多所謂嚴肅號,嘴上主義,心里生意,還偏要包裝出一套“對讀者友好”“擁抱變化”等話術,自我美化,只想點上一首《浮夸》送給諸位老師。
其實很感激新媒體這份職業,它讓我在北京有一份還算體面的生活姿態,讓我見到很多了不起的人,收到了很多認可,獲得了很多不敢想的機會。可是隨著我所謂的,在文字處理、報道領域認知上的進步,我以為能克服的東西卻更加鼓噪——你做的這些,真的有一絲一毫意義嗎?我所有的困惑,真的只是源自我的幼稚與蜜汁優越嗎?
寫作是一場修行,但新媒體對我來說,可能真的不是一個好道場。
5、
ID:木蘭花
星座:摩羯
新媒體方向:TMT與泛娛樂
“也許是討厭工作,不是討厭自媒體。”
出于禮貌,做自媒體的同行都互相稱一句老師,即便從來沒有聽說過彼此所在的公眾號,也沒有看過各自寫的任何文章。蝦兵蝦將,魚龍混雜,我就是那個不知名的小透明。
換以前,可能會不舒服,現在不會,很少感受到冒犯。畢竟,我也經常在聽完別人介紹后,腦子一片空白:什么號,做什么的?倉皇之下,不敢追問,最后假裝自己聽清楚了,聽明白了,微笑寒暄,加個微信,有機會約飯。
類似的場合很多。因為基本沒有自媒體會接觸社會新聞,膽子大的,撐死做做評論,自媒體老師見面的場合,多是干干凈凈的酒店。觥籌交錯,推杯換盞,一天下來,好像還應該出門跑兩圈,運動量不大夠。
每一場活動,都能多認識幾個自媒體作者,社交是對一場活動最大的尊重。不知道有多少做媒體的人,會在私下說,自己有社交恐懼癥。我挺典型的,采訪的時候,會拿出不正常的熱情,讓談話不尷尬,好像什么都能聊。
實際上,微博上經常調侃的那種,能發微信堅決不語音的人,就是我。打陌生的采訪電話前,還會深呼吸好幾次,采訪一結束,感覺全天的能量,都用到了電話上。

自媒體是一個社交重于很多東西的地方。雖然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社交,絕對不是酒店換個微信號碼,換出來的。但社交永不止步,不分場合,不分時間。
自媒體號的創始人尤其明白社交的重要性,有時候一個事兒能不能辦成,主要還是得益于人脈圈子夠不夠廣。進一個圈子就要適應一個圈子的規則。
所以老板經常鼓勵大家出去社交。
認識人,也讓別人記住你。自媒體和傳統媒體特別的不一樣,傳統媒體的很多老師,就埋頭寫稿,不太注意個人形象或者,高級一點講,叫個人品牌。
不是說,傳統媒體就沒有老師在做自我的包裝,而是從大的環境里來看,傳統媒體的記者,更像以前的文人,不太懂營銷那一套。
學會自我的推銷,是非常健康正常的事情。但于我來說,還是需要打破很多的心理障礙。一點一點的說服自己,去接納這些新的工作方式。
我絕對不是一個典型的90后。我對于新事物的接納能力,低于這個年齡段的平均水平。以上很可能只是借口,沒準只是我自己還做不好事,沒辦法實現迅速成長,換來成就感。
最絕望的一個事兒,還沒聊,也是最近讓我感到非常困擾的事情。做自媒體的應該很清楚,就是流量。傳統媒體被流量打趴下了。自媒體的創始人,在說自己尊重好內容的同時,逐漸的成為流量的俘虜。畢竟流量就跟國家的GDP一樣,誰都需要這個面子。
很多人都愛說,稿子沒有流量,說明你稿子寫的不好。我會給這個結論打個問號。我見過太多寫的好的文章沒有流量。因為那些人不會運營。
我最怕流量的地方在于,這東西會讓人變得懶惰。流量的情緒點,比其他的寫作、采訪上的東西,更容易上癮,也更容易掌握,甚至會變成一個作者衡量自己的一把尺子。
以前做選題,除了去看一個新聞可能獲得的流量,還會思考,本身的社會價值,評估一個選題的尺度是非常多元的。領導也會支持去做這些嘗試。
現在,當你提出質疑的時候,會最先受到質疑,你不懂流量,你稿子不夠好。但是又沒什么資格不工作,只能不斷去適應新的規則。內心不夠強大,永遠在退讓。
以后還做自媒體么,心里不太愿意,但可能本身的選擇也不多。
寫在最后
說實話,報這個選題的時候,娛sir只是想找幾個心態游離的同行吐吐槽,大家自嘲一下,其樂融融。
我們也不是想講述一個滿懷理想的青年是如何被惡劣行業教育的俗套故事——主題的限制讓文章的觀點天然帶有“幸存者偏差”,而五位新媒體人當中,畢業最久的也不過4年。
但到了這里,忽然發現在戲謔之外,還多了一點其他的東西——那些面對流量時的困惑感、失落感與不甘心。
娛sir無力根據他們的故事指指點點一番,只知道很多東西確實如同他們描述的那樣,被瓦解掉了,被地鐵上響徹無數耳機的羅振宇們瓦解掉了,被咖啡店里比較微信抖音宣傳效果的聲音瓦解掉了,被朋友圈刷屏爆款文瓦解掉了。
所以問題又回到了原點:在高歌猛進的時代,把那些“不聰明”的人、那些自命不凡的人、那些心懷警惕的人、那些自作主張的人,連同他們的困惑失落不甘心,一起施行淘汰,世界就會變得更好嗎?
經授權轉載至數英,轉載請聯系原作者
作者公眾號: 娛樂產業(ID:娛樂產業)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范轉載侵權必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授權事宜請至數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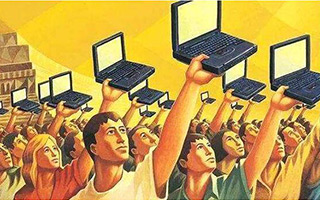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全部評論(4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