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后廣告時代:多家入局,玩法混沌,好像和19世紀也沒啥兩樣
作者:騰訊傳媒,來源:全媒派
2018年的全球新聞業甚為艱難。
Vox Media,Vice和BuzzFeed這些一度充滿活力的年輕媒體,都在2018年經歷了裁員的浪潮。

Mic,曾經價值1億美元的媒體,由于2018年11月底Facebook終止與其在社交網絡上發布視頻的合作協議,Mic在短時間內解雇了大部分員工,并以僅僅5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
同樣是2018年,美國最大的電信運營商Verizon對其數字媒體部門進行了近50億美元的資產減記。
而路透社則宣布計劃在接下來兩年里裁員3200人。
——寒冬之中,幸存者寥寥。裁員和賣身越來越成為繞不開的話題,在如此的艱難時刻里,媒體對廣告商的吸引力不斷下降。
人們往往通過表象推斷,平臺“贏家通吃”的局面是谷歌和Facebook建立起雙頭壟斷的必然結局。畢竟,目前超過50%的數字廣告收益都流向了這兩家公司,并且它們還控制著90%的廣告收入增長收益。

但表象之下暗流洶涌,事實遠比大多數人所以為的更為復雜。本期全媒派編譯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分析到底是什么讓媒體失去廣告、一步步走入寒冬,而廣告的減少又會為新聞業未來的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
一、更多的入局者
Facebook和谷歌看似在廣告收入方面風光無限,但它們的壟斷地位遠遠沒有人們想象得那樣堅固。事實上,幾乎每一個大型科技公司在廣告銷售方面都是Facebook和谷歌的潛在競爭對手。
亞馬遜的廣告業務在過去一年中爆炸式增長,甚至超過了雙寡頭。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蘋果也在技術端持續發力,以爭奪來自Snapchat和Pinterest等主要應用的廣告收入。此外,LinkedIn和Bing的發展則幫助微軟在2018年獲得了約40億美元的廣告收入。
瓜分廣告蛋糕的絕不僅是頂級巨頭們。優步也將發展廣告業務,以新的收入來源迎接即將到來的上市。AT&T正在建立一個廣告網絡,來配合其對時代華納內容產業的投資。而銷售流媒體電視設備的Roku也正在構建廣告技術。同時,Axios的報道則稱,Oracle,Adobe和Salesforce都在使用他們的云技術來收集可用于廣告定位的數據。

相比于將傳統新聞采集作為核心業務的媒體,這些科技公司擁有更多用戶,也掌握更多用戶數據。因而對于廣告投放者來說,這些匯集用戶、提供技術服務的科技公司無疑是性價比更高的選擇。
二、匱乏的資金來源
隨著越來越多的廣告告別媒體版面、遷移到數字平臺,媒體的資金來源不斷縮窄。曾經閃現的一縷縷希望,事后證明要么只是短暫的春天、要么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
iPad端的用戶閱讀量在數年前一度為媒體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可這種曇花一現的高光時刻沒有永駐。曾經被寄予厚望的iPad終究不是媒體的救世主。

風投也無法充當為媒體帶來轉機的角色。當各種聲音都在唱衰媒體時,風險資本自然也不是有力的依靠。既然媒體無法像科技公司一樣創造利潤回報,它也就無法被風投青睞、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
一部分人認為地方新聞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應該獲得公共援助,比如政府補貼。但至少目前,這種期待還無法落地生根。
三、迷茫的商業模式
在前所未有的變局之中,新聞媒體也在進行著一切可能為他們帶來轉機的試驗。
最廣泛的實驗莫過于付費墻。在過去兩年中,許多報紙和雜志都嘗試通過內容付費訂閱的模式來來自彌補廣告商的收入損失。除了相對常規的訂閱制,包括The Atlantic和The Correspondent的一部分報刊還探索了更加“高階”的會員制來滿足鐵桿讀者的需求。

除了圍繞內容本身的盈利模式,各家媒體也押寶多元化經營。全媒派往期文章《<紐約時報>押注多元化經營:販賣生活方式,全面入侵讀者日常》介紹了《紐約時報》是如何通過為讀者提供理財建議和生活指南來踐行其多元化經營戰略的。此外,BuzzFeed也多途徑開源,在紐約開設了一家商店,與沃爾瑪合作出售廚房用品,以期跳出來自新聞的單一收入結構。

媒體也嘗試通過視頻來自救。全媒派往期文章《新聞業X鎂光燈:報道的第N+1種輸出可以成功突圍嗎?》介紹了媒體與影視機構合作的可能性。但這可能并不足以為媒體帶來春風——畢竟,本文開頭所提到的Mic的前車之鑒告訴我們,一旦平臺改變其分發內容的策略時,這些媒體所賴以生存的商業模式可能立刻土崩瓦解,最后逃不開大幅裁員、廉價賣身的下場。
四、靠不住的金主爸爸
金主投資確實能夠為少數的媒體帶來長久繁榮。由Salesforce的創始人馬克?本尼奧夫收購的《時代周刊》,由泰國商人謝展(Chatchaval Jiaravanon)收購的《財富》和亞馬遜創始人杰夫·貝佐斯收購的《華盛頓郵報》都讓人們看到,億萬富翁可能真的能讓個別幸運的媒體走出寒冬。

可是富翁的贊助可能也帶來諸多問題。贊助通常是基于一個人的想法,而一個人可能改變自己的想法。比如,邁克爾·布隆伯格曾說過,他如果競選總統,可能就會拋售彭博社這樣一個龐大的媒體帝國。富商收購并不是通用且完美的解決方案。
五、后廣告時代,媒體何去何從?
新聞業發展的道路難以具體地預測,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媒體會打造出內容訂閱、贊助和多元化經營相協調的收入結構,廣告在媒體營收中肯定會發揮越來越小的作用。
要了解后廣告時代媒體的未來,我們需要回顧它的過去。政黨報刊盛行的19世紀初期,報紙依賴政黨的贊助。因此報刊的內容也以發表對政黨有利的信息和觀點為主,攻擊競爭對手是主要的目的。

美國政黨報紙National Gazette
那個時代的新聞業以政治為中心的,而且存在深深的偏見。但是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政黨報刊也具有很大的價值。美國的報紙數量從18世紀后期的幾十家增長到19世紀30年代的1200多家。這些報紙嘗試了各種新聞風格來吸引公眾,正如華盛頓大學教授Gerald J. Baldasty所說,這些報紙將讀者視為一個公民團體,不斷吸引和激勵他們。也許因為如此,美國的投票率在19世紀中葉飆升至歷史新高。
而正是廣告加速了政黨報刊的消亡。廣告允許報紙經濟獨立,離開政黨的控制,從此建立更加專業客觀的現代新聞標準。廣告的興盛也帶來了一種新的報道風格,記者們會在報道中避免冒犯最大的廣告商,比如大型百貨公司。
隨著媒體的收入來源從廣告商轉移到贊助人和讀者(也就是訂閱者),新聞業可能會逃脫來自廣告商的無形束縛,以更加直接、中立的方式報道這個世界。新聞業可能會再次變得更具政治性,但也會更具吸引力。
——這已經是趨勢本趨。
例如,在過去幾十年中,《紐約時報》的收入已從超過60%的廣告轉移到超過60%的來自讀者的內容付費。隨著其商業模式的變化,報紙的風格也在發生變化。已故的威斯康星大學教授James L. Baughman認為,“與2010年相比,1960年的《紐約時報》有著更強的闡釋性”。
對于媒體,如今付費讀者和科技公司的地位就如同上世紀的百貨公司、19世紀的政黨,因為他們都是媒體賴以生存的主要收入來源。而這種轉變會落實在報道的字句之中,為新聞內容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過去已死,無可轉變。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新聞業正從20世紀中旬的“黃金時代”中走出,奔向一個焦慮與興奮共存的未來。
經授權轉載至數英,轉載請聯系原作者
作者公眾號:全媒派(ID:quanmeipai)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范轉載侵權必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授權事宜請至數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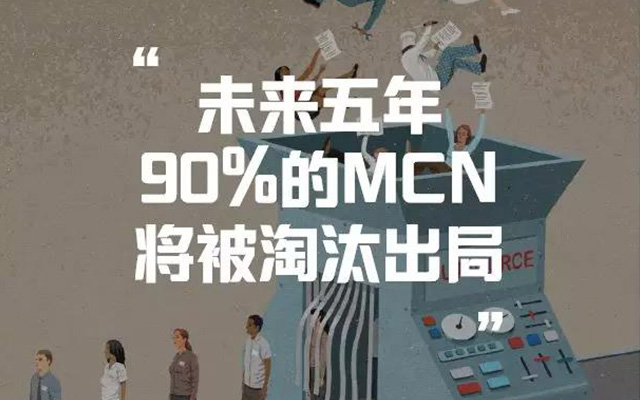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全部評論(1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