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shù)字時代新階級:平等的互聯(lián)網(wǎng)讓世界更不平等了嗎?

來源:全媒派
第四季《奇葩說》有個辯題,討論“是否應(yīng)該支持讓全人類一秒知識共享的技術(shù)”,反方辯手詹青云的一段發(fā)言把比賽推向高光時刻。
我們今天,不是活在一個知識被縮在廟堂里的時代,我們活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一個知識生產(chǎn)的速度超越我們儲存它速度的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考驗的,恰恰是你從這些知識當中,去挑選、辨別、排序的能力。這種能力,是熟能生巧的直覺,它是不可以被存進芯片的。

這正是我們所處的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啊。
鼓吹平等的互聯(lián)網(wǎng)上可以搜索到所有開放信息,某種程度上看,它的確讓世界變得更公平了。普通人可以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找到頂尖學(xué)府如哈佛、清華的公開課,也可以在專業(yè)平臺如得到和喜馬拉雅買到所謂知識和內(nèi)容,而在整個互聯(lián)網(wǎng),包括各類聚合資訊平臺和社交媒體,有足夠多免費的泛資訊內(nèi)容。獲取資訊似乎變成了毫不費力的事情。
然而,如何從這些信息中揀選出必要內(nèi)容就成了一門必修課。內(nèi)容產(chǎn)品絞盡腦汁說服用戶:我給你的內(nèi)容是最好的,比如付費。這或許是篩選信息的一重濾網(wǎng)——用金錢購買別人的智慧,比如財新、得到;或是編輯篩選,過濾了低價值用戶和資訊,比如早期采用邀請制的“知乎”和現(xiàn)在的邀請制小程序“頭牌觀點”。
上網(wǎng)成了升級打怪,搜索能力、付費能力、篩選能力是一個個等待解鎖的技能包。裝備不同,獲得的成績和回報千差萬別。
這個時代,老生常談的“知溝理論”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嚴重,數(shù)字鴻溝也并沒有因技術(shù)普及得到緩解。看似公平的互聯(lián)網(wǎng)把用戶分出了貧富階級,一邊是因為地區(qū)和個體收入水平差異,用戶被動地被劃分成所謂“五環(huán)內(nèi)外”,另一邊是被海量信息裹挾但篩選能力差異化的用戶,主動強化著階級屬性。
一、被地區(qū)與個體收入水平差異割裂的互聯(lián)網(wǎng)階級
從全球范圍來看,區(qū)域發(fā)展不均衡嚴重影響信息的平等傳遞。縮小范圍至個體收入水平,信息提供者也在加劇這種不公平。
Web Foundation在今年10月發(fā)布全球互聯(lián)網(wǎng)報告:全球接入互聯(lián)網(wǎng)的用戶增長出現(xiàn)大幅下滑。這并非意味著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已經(jīng)進入了飽和狀態(tài),恰恰進一步說明了數(shù)字鴻溝的存在:當冰島地區(qū)在2016年就達到96.2%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率時,東非的厄立特里亞國只達到1.2%。

在這些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率極低的國家,“全球互聯(lián)”對他們而言似乎是天方夜譚。
號稱是“自由的百科全書”的維基百科首頁,列出了幾大語種的詞條數(shù)。英語條目以576萬居于榜首,其次是德語和法語條目。俄語、西語、中文、日語均被列出,但更小或更落后的如東南亞、南亞和非洲國家,要想找到以該國母語列出的條目卻要費些勁。

維基百科打造的,本應(yīng)該是一個開放平等的知識共享社區(qū)的維基百科,詞條編輯由用戶眾包完成。但在經(jīng)濟欠發(fā)達的地區(qū),有時間、有資質(zhì)承擔(dān)“志愿工作”的用戶遠低于發(fā)達地區(qū)。
據(jù)《好奇心日報》報道,維基百科社區(qū)一年一度的大會 Wikimania 2018 上,一位非洲編輯質(zhì)疑道:“你指望我們志愿免費貢獻我們的知識嗎?這里的人甚至無法志愿貢獻時間。”維基百科所奉行的無償編輯在全球范圍內(nèi)也并沒有普適性,“社會經(jīng)濟環(huán)境可以改變一個國家在網(wǎng)絡(luò)知識產(chǎn)出上的能力”,但不是所有人都享受著經(jīng)濟發(fā)展的紅利,因而有時間在維基寫詞條。
小國和欠發(fā)達地區(qū)的關(guān)注度不會太高,我們似乎默認了這一條規(guī)則,但深究起來,硬件條件、貢獻者數(shù)量和知識水平的差異終于通過百科條目外化了。
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蘋果公司的新聞產(chǎn)品Apple News。這個自2015年啟動的項目,匯聚了30多名曾經(jīng)的一線記者和編輯,試圖用“蘋果的技術(shù)+編輯的智慧”打造一款精品資訊應(yīng)用。但3年過去,也只有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三個地區(qū)的用戶可以使用。
盡管商業(yè)世界自有其規(guī)則和考量,但這種“限定發(fā)售”的形式,很難說不是在加劇著信息的獨裁與壟斷。

Apple News總編勞倫·科恩(Lauren Kern),曾任《紐約時報》雜志部門擔(dān)任副主編、《紐約》雜志主編
而個體收入水平的差異決定了他們對接收的信息質(zhì)量的期待,反過來又影響著信息生產(chǎn)者的目標定位。
《經(jīng)濟學(xué)人》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這個時代的注意力是否已經(jīng)被貨幣化?
文章采訪到《注意力商人》作者Tim Wu:“如果你不為此付費,那你的注意力就會變成產(chǎn)品(If you’re not paying for it, you might be the product)。”
艾瑞咨詢發(fā)布的《2018中國在線知識付費市場研究報告》中,預(yù)測知識付費的規(guī)模將從2017年的49.1億增長到235.1億,知乎、得到、千聊、喜馬拉雅等頭部產(chǎn)品的市場規(guī)模日漸擴大,更細分的中腰部產(chǎn)品也在搶占著市場份額。但與此同時,極光大數(shù)據(jù)發(fā)布的《2017知識付費類App研究報告》也顯示,知識付費的消費主力更多集中在一、二線城市,總體收入水平差異直接體現(xiàn)在對優(yōu)質(zhì)信息的購買力上。

在《經(jīng)濟學(xué)人》的采訪中,Tim Wu還提到,質(zhì)量過硬的產(chǎn)品只會因消費者的支付行為而存在,因為編輯的目的在于獲得用戶認可,而不是注意力。
那么,不愿意付費或無能力付費的用戶,只能拱手交出自己的注意力。不論是Facebook、谷歌,還是趣頭條和今日頭條,它們始終攥著“時間不值錢”的用戶的注意力,用海量水平參差的信息轟炸出新的數(shù)字階級。
二、 當然,也有人正在主動固化數(shù)字階級
上周,冰點周刊刊發(fā)的《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在朋友圈刷屏,有人感慨:技術(shù)終于填平了數(shù)字鴻溝,貧困縣里也走出了省狀元。后續(xù)的媒體報道卻越來越多地揭示了這塊屏幕的問題:比如學(xué)生的知識水平跟不上,“這塊屏幕”對他們而言或許是雪上加霜。
放大來看,面對繁雜信息,篩選能力各異的普通人同樣如此。
酷鵝用戶研究院今年8月發(fā)布《三四線用戶內(nèi)容消費洞察報告》,三、四線城市用戶明顯更偏好于趣頭條、天天快報等聚合型產(chǎn)品,一、二線城市用戶則更偏向鳳凰新聞、搜狐、網(wǎng)易、好奇心日報和即刻。前者的邏輯偏向于算法分發(fā)和“被動投喂”,用接地氣的內(nèi)容和網(wǎng)賺形式吸引用戶;后者則是自主生產(chǎn)和用戶主動篩選,既要求用戶有一定的信息消化能力,也需要一定的篩選能力。

正如前文所說,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獲取信息的方式變得便捷和廉價了許多,但內(nèi)容消費的渠道和姿勢所造成的馬太效應(yīng)依然無可避免。階級固化似乎從來不因技術(shù)進步得到緩解,反而越發(fā)極端化。
40年前,傳播學(xué)者P.J.蒂奇諾提出“知識溝假說”時,認為隨著大眾傳媒向社會傳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會經(jīng)濟狀況較好的人將比社會經(jīng)濟狀況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這類信息,因此,這兩類人之間的知識溝呈擴大而非縮小之勢。
當時,意在為貧困家庭兒童提供補充教育而制作的動畫片《芝麻街》,播出后的結(jié)果卻是:對節(jié)目接觸和利用最多、產(chǎn)生更好效果的仍然是富裕家庭的兒童。因此它不但沒有縮小不平等,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擴大了差異。
但40年之后,經(jīng)濟貧富依然決定著信息貧富。
全媒派曾編譯《紐約時報》的“新貧富數(shù)字鴻溝”一文,調(diào)查顯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平均每天在“屏幕”上大約花費8小時7分鐘,而來自更高收入家庭的同齡人大約只花5小時42分鐘。而在同一個社區(qū)里,受硅谷精英青睞的私立學(xué)校Waldorf,你找不到一臺電腦或是其他電子設(shè)備;而附近的Hillview公立中學(xué)卻在宣傳它的iPad教育計劃,在這里學(xué)習(xí)的孩子將人手一臺iPad并把它當做必不可少的學(xué)習(xí)工具。
看,技術(shù)的普惠并沒有消弭階級的差異。
以往的知識溝把能接觸技術(shù)產(chǎn)品的精英家庭和不能接觸技術(shù)產(chǎn)品的普通家庭劃在兩邊。如今,這兩撥人之間依然有一條鴻溝,只不過,精英家長們已經(jīng)開始同電子產(chǎn)品劃清界限,普通家庭剛剛趕上他們40年前的步伐。
信息篩選和吸收的能力成了數(shù)字時代突破階級的必備技能包。
闌夕在一篇文章里寫到,今日頭條和抖音是為“延遲滿足能力低下”的用戶服務(wù)的。事實上,今日頭條也好,微博、微信也好,內(nèi)容產(chǎn)品無一不在考驗我們的鑒別技能。要不然為什么都是交費上網(wǎng),得到的收獲如此萬千。
微博網(wǎng)友@老西醫(yī)概括稱:無論哪里,非頭部的信息提供和分發(fā)者,只能算沉迷者的人大致都可以說是屌絲吧。

清華大學(xué)彭蘭教授在《網(wǎng)絡(luò)社會的網(wǎng)民素養(yǎng)》一文中提出“網(wǎng)絡(luò)信息消費素養(yǎng)”,包括在網(wǎng)絡(luò)中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對網(wǎng)絡(luò)信息的辨識與分析能力,以及對網(wǎng)絡(luò)信息的批判性解讀能力。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信息貧困”差異。
至少,面對信息過載,信息富人們突破數(shù)字階級的可能總是要大一些的。
在那場關(guān)于“知識共享”的辯論上,薛兆豐教授問高曉松:“那個(一秒實現(xiàn)共享的)芯片和現(xiàn)在的互聯(lián)網(wǎng)有什么區(qū)別?”高曉松回答:“互聯(lián)網(wǎng)需要時間。”但是,“不需要時間就進你的腦子,那是平等的垃圾。”
開放的互聯(lián)網(wǎng)讓世界更平等了嗎?或許,只是換上所謂“公平”的外衣,極化了數(shù)字時代的新階級。

參考資料:
1. The Economist:Has our attention been commodified?
2. 彭蘭:網(wǎng)絡(luò)社會的網(wǎng)民素養(yǎng)
3. 極光大數(shù)據(jù):知識付費類app研究報告
4. The Guardian: Exclusive: dramatic slowdown inglobal growth of internet access
5. 好奇心日報:維基百科“知識平等”不僅沒有實現(xiàn),還是現(xiàn)實不平等的映射
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至數(shù)英,轉(zhuǎn)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
作者公眾號:全媒派(ID: quanmeipai)
轉(zhuǎn)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jié)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未經(jīng)授權(quán)嚴禁轉(zhuǎn)載,授權(quán)事宜請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quán)必究。
本文禁止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授權(quán)事宜請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quán),侵權(quán)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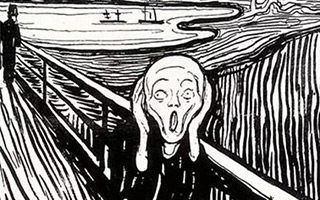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暫無評論哦,快來評論一下吧!
全部評論(0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