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站評分9.9,《中國奇譚》造了一面能探見人心的鏡子
《中國奇譚》開播一個(gè)月,火了一個(gè)月。
#中國奇譚封神#
#中國奇譚豆瓣開分9.5#
#中國奇譚小廟原型#
#中國奇譚周邊賣斷貨#
......
即便中間不乏有春節(jié)檔電影吸引注意力,這一以志怪故事為主題的國產(chǎn)動(dòng)畫短集的熱度依舊不減。從觀眾對故事情節(jié)寓意的探討,對動(dòng)畫、海報(bào)視覺的稱贊,以及人們時(shí)常被細(xì)節(jié)畫面觸動(dòng)的反響來看,《中國奇譚》無疑迎來一個(gè)成功的開局。

“出道即封神”的《中國奇譚》“神”在哪?
一、視覺盛宴,熟悉而陌生的味道
1922年,一部時(shí)長只有1分鐘的動(dòng)畫廣告片《舒振東華文打字機(jī)》掀開了中國動(dòng)畫的第一頁。此后的很長時(shí)間,中國動(dòng)畫迎來繁榮期,百花齊放的文化氛圍中,上海美術(shù)電影制片廠創(chuàng)造了太多輝煌:我國首部彩色木偶動(dòng)畫《小小英雄》,首部剪紙動(dòng)畫《豬八戒吃西瓜》,首部水墨動(dòng)畫《小蝌蚪找媽媽》......而《大鬧天宮》《葫蘆兄弟》等經(jīng)典動(dòng)畫更是跨越代際的經(jīng)典之作。
2023年,在中國動(dòng)畫新的100年的起點(diǎn),同樣由上海電影美術(shù)制片廠出品的《中國奇譚》又把人們拉回到熟悉的記憶原點(diǎn),由8個(gè)故事組成的動(dòng)畫短集,采用了8種不同的風(fēng)格,素描、剪紙動(dòng)畫、偶定格......這似乎是對中國動(dòng)畫上一個(gè)百年的致敬,也讓人感受到在視效技術(shù)發(fā)達(dá)的今天,創(chuàng)作者精耕傳統(tǒng)技藝的匠心與誠意。僅僅是海報(bào)便足以抓住觀眾的眼球,除了直觀可見的視覺美,藏于“形”之后的東方神韻亦令人贊嘆。
這部作品,總導(dǎo)演陳廖宇和團(tuán)隊(duì)成員準(zhǔn)備了兩年,“精益求精”體現(xiàn)在方方面面。上海美術(shù)電影制片廠的前輩們給出的建議,也細(xì)致到“煮唐僧的鍋,似乎普通了點(diǎn)”這樣的程度。《鄉(xiāng)村巴士帶走了王孩兒與神仙》對窗臺、老屋、土地廟等多個(gè)場景的刻畫都讓觀眾直呼“和小時(shí)候我家一模一樣”。

《小豬妖的夏天》煮唐僧肉用的鍋
《鄉(xiāng)村巴士帶走了王孩兒與神仙》中的院子
此外,《中國奇譚》的許多細(xì)節(jié)都體現(xiàn)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借鑒與傳承,比如《鵝鵝鵝》中狐貍書生的形象借鑒了京劇臉譜藝術(shù),頭戴簪花也是唐代男子流行的裝束。《小滿》中集市的場景是對古畫的演繹。

《鵝鵝鵝》狐貍書生形象

《小滿》畫面
除了風(fēng)格鮮明的具象表達(dá),《中國奇譚》中一些抽象之筆和留白處理也起到畫龍點(diǎn)睛的作用。《小豬妖的夏天》中,最后唐僧師徒四人只是以輪廓初現(xiàn),給觀眾帶來無盡遐想空間的同時(shí),也保留了各自對孫大圣獨(dú)有的印象。這種熟悉又陌生的味道勾連起每個(gè)人的內(nèi)心,產(chǎn)生奇特的共鳴感,這也許就是好作品的魅力。

二、志怪故事新演繹,串聯(lián)貼切的人生課題
除了畫面的美感,故事的平實(shí)真切更打動(dòng)人心。如同動(dòng)畫名所示,《中國奇譚》講述了 8個(gè)帶著怪誕、奇幻色彩的故事,區(qū)別于傳統(tǒng)志怪故事給人留下的驚悚刺激印象,《中國奇譚》弱化對“妖”的刻畫,從人的角度,用簡約的對白、平和的敘事呈現(xiàn)的更廣范疇的“妖”,即人心。故事里的“妖”作為情節(jié)的牽引線,給觀眾營造出適當(dāng)?shù)幕恼Q、恐怖氣氛,但關(guān)于人的敘事,則要復(fù)雜得多,溫暖、純真、邪惡、迷茫、彷徨、愛與孤獨(dú)......不同的心念交織在一起,隨著故事進(jìn)展一同跌宕起伏,幾經(jīng)拉扯最后讓人恍然大悟,相比妖,更可怕的是人的「心魔」。觀眾看的是關(guān)于妖的故事,也在看平時(shí)自己不愿意面對的錯(cuò)綜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
所謂“奇譚”,自然是蒙上一層虛幻未知色彩,而這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與其說我們在看傳說中的妖,不如說在觀真實(shí)的自己。故事有結(jié)局,但那些蘊(yùn)藏其中、幾乎每個(gè)人都要面對的人生課題卻需要用漫長的一生去探索——
課題一:理想與現(xiàn)實(shí)
看完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許多觀眾都會發(fā)出“小豬妖在演我”的感慨,這種共鳴源于導(dǎo)演對普通人的工作、生活近乎復(fù)刻般的呈現(xiàn)。小豬妖只是一只沒有法力、在浪浪山干著無關(guān)緊要雜活的底層小妖,與人的世界一樣,他也會一邊懷疑意義一邊為了生活接受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會面臨辛苦做出的更好方案被無情否定的情況。而無論小豬妖多么普通,他的媽媽依然以他為榮,一面念叨著小豬妖要照顧好自己,一面往他的葫蘆里灌滿水。妖與人的界限在這里變得模糊,在褪去魔法的外衣后,妖離人更近,人也離真相更近,進(jìn)而引發(fā)關(guān)于人生抉擇等更深維度的思考。



在我看來,小豬妖、浪浪山、水葫蘆分別代表了自己、現(xiàn)實(shí)和家,浪浪山之外的世界,或許每個(gè)人都曾渴望過,但是有勇氣真正行動(dòng)起來走出去的人卻很少,畢竟面對未知,我們無法計(jì)量自己是否能承擔(dān)起不確定性帶來的風(fēng)險(xiǎn)。正如小豬妖在出逃的過程中,前有不明方向的路,后有狼大人的窮追不舍,這段路,的確需要勇氣。讓人松一口氣的是,導(dǎo)演於水給了故事一個(gè)溫暖的結(jié)局。小豬妖最終歷經(jīng)險(xiǎn)阻,遇上唐僧師徒四人,孫悟空將計(jì)就計(jì)假裝打死給他們發(fā)送“不要過來”信號的小豬妖,又在其他妖怪被除掉后拉起小豬妖并給了他三根“保命汗毛”,這一幕仿佛讓觀眾心中的希望又重新燃起,相信善意,拾起改變、逐夢的勇氣。
課題二:欲望與自我
相比第一集的直白呈現(xiàn),《鵝鵝鵝》和《林林》在思想表達(dá)上更為隱晦。這兩個(gè)故事雖然主題不同,但都照見了人內(nèi)心隱秘的角落。欲望貪婪而猙獰的面孔,因?qū)で笳J(rèn)同而迷失的自我,在這兩個(gè)故事中得到極致的體現(xiàn)。
《鵝鵝鵝》的表現(xiàn)形式比較特殊,全程沒有對話,而是以簡短的話語作為線索,串聯(lián)起故事本身,每句話的主語都是“你”,給觀眾帶來了一場沉浸式的體驗(yàn)。故事很簡單:背著兩只鵝的貨郎在途經(jīng)鵝山時(shí)遇上了怪異的狐貍書生,并在他的驅(qū)使下偏離原來道路、去往新的山頭,最終丟掉了鵝也不再是來時(shí)的自己。結(jié)尾處,留下狐貍書生的邪魅一笑和一句意味深長的的話:“你是個(gè)貨郎,就在剛剛,你丟了三只鵝。”


至此,狐貍書生離去,山頭的美酒、美人也消失,只留下貨郎獨(dú)自一人悵然若失,屏幕前的觀眾長舒一口氣,仿佛從一場緊張的夢中清醒。狐貍書生如同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欲望,能迷惑人、指使人走入幻象的深淵而不自知,當(dāng)幻境消失才發(fā)現(xiàn)初心早已被欲望吞噬,而那個(gè)和自己最初夢想如此相近的“第三只鵝”也終究是你抓不住的虛妄,忘記自己來時(shí)路的人亦如同大夢一場空。

如果說《鵝鵝鵝》是自我與外界的極限拉扯,那《林林》則是自我一體兩面的對抗。“我”是人,林林是狼,在那片森林,人與狼的界限分明,大人們告誡孩子不要去對面那個(gè)不屬于人類世界的叢林,狼媽媽也總讓林林不要靠近人。然而無論是人類的小孩還是化作女孩樣貌的林林,都絲毫沒有覺得彼此有什么不一樣并試圖成為好朋友。為了證明自己和其他人一樣,林林將狼媽媽的告誡拋諸腦后,前往人類家中做客,最后在獵人的試探與圈套中暴露自己的“不一樣”。林林逃走,獵人追殺,誰也沒有勝利。

“我”試圖走進(jìn)林林的世界,林林一直想證明自己和別人是一樣的以融入人類的世界,似乎他們都在尋求他者的認(rèn)可。長大后的“我”再沒見過林林,而自己穿上農(nóng)具留在雪地上的腳印卻如此像狼的腳印,緊接著鏡頭轉(zhuǎn)換,“我”和狼隔著一條小溪平靜對視。此時(shí)狼不再是人形,“我”也不是與狼勢不兩立的獵人,兩者中間依然有象征界限的溪流,但卻沒有了對抗。我想,“我”和狼或許本是一體,當(dāng)自我認(rèn)同缺失,個(gè)體的內(nèi)在便會擰巴、抗?fàn)帲屪约焊械酵纯啵?dāng)內(nèi)在安定、協(xié)調(diào),個(gè)體也就恢復(fù)平和,人與狼的戰(zhàn)爭實(shí)則是一趟關(guān)于認(rèn)識自我、接納不同的人生課。


課題三:成長與告別
有人說:“你無法同時(shí)擁有童年和對童年的感受。”也許,長大就是一個(gè)一邊向前一邊回望的過程,透過記憶我們能從溫潤的往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又總能捕捉到對過去某段時(shí)光新鮮的認(rèn)知,時(shí)間更替、新舊交織,我們獲得一些又失去一些,而后塑造了現(xiàn)在的自己,這大概就是成長。《小滿》和《鄉(xiāng)村巴士帶走了王孩兒和神仙》從不同角度向我們展示了這段歷程中的得與失。

長大后的小滿知道自己噩夢中的“妖”只是一條普通的魚,曾經(jīng)的恐懼感消失,但隨之消失的也有童年時(shí)對未知的好奇和無邊的想象力。鄉(xiāng)村巴士帶走王孩兒和神仙時(shí),也帶走了一些純粹的堅(jiān)持與信仰,劉先生沒再看見三個(gè)影子,講著關(guān)于那座山里妖怪故事的老人們也逐漸離去,隨之離去的也有劉先生兒時(shí)那股對神秘力量強(qiáng)烈的探知欲。村子還是那個(gè)村子,但人事物都已不同,最后在雪地上點(diǎn)燃竄天猴的劉先生在想什么呢?也許是與過去的告別,也許是又有了找尋新的堅(jiān)守與純真的熱情。


小時(shí)候的我們對故土以外的世界充滿想望,長大后又對回不去的故鄉(xiāng)滿是眷戀,若成長與告別不可避免,那依然葆有一份對寧靜的向往和對簡單的追求也是一種慰藉。


三、未完,待續(xù)
相比“封神”、“巔峰”、“崛起”等字眼,我更愿意用“開始”來形容這部給人帶來驚喜的動(dòng)畫短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中國奇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實(shí)驗(yàn)與探索,這是傳承但不是回歸,畢竟時(shí)代車輪滾滾向前,如同一切向上生長的新鮮事物一樣,更上一層樓也是中國動(dòng)畫的必然使命。所幸,在《中國奇譚》中我也看見那些與新時(shí)代、新情境緊密相連的情緒與議題。當(dāng)然,無論如何更新變換,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和人們關(guān)于“美”的共通性不會改變,它們構(gòu)成了好作品的內(nèi)核,這也是《中國奇譚》打動(dòng)我的重要因素。
《中國奇譚》會有續(xù)集,相信中國動(dòng)畫的輝煌也未完待續(xù)。
你看《中國奇譚》了嗎,歡迎評論區(qū)交流對故事不同的理解哦~
轉(zhuǎn)載請?jiān)谖恼麻_頭和結(jié)尾顯眼處標(biāo)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未經(jīng)授權(quán)嚴(yán)禁轉(zhuǎn)載,授權(quán)事宜請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quán)必究。
本文禁止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授權(quán)事宜請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quán),侵權(quán)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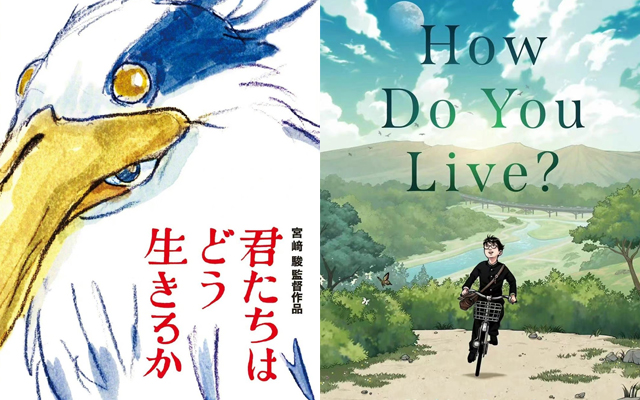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全部評論(5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