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dle退出中國,劉強東沒說錯

作者:何劦,編輯:張軼驍,來源:鳳凰WEEKLY財經
“閱讀神器”Kindle,退出中國倒計時正式開啟。6月2日下午,Kindle官方通知,自即日起,亞馬遜將會停止向經銷商供應新的Kindle電子書閱讀器,并將于2023年6月30日在中國停止Kindle電子書店的運營。
2023年6月30日之后,亞馬遜將停止Kindle電子書的購買功能,用戶將無法再購買新的電子書。2024年6月30日之后,用戶將無法再下載已購買的電子書,但已經下載的電子書可以繼續閱讀。
早在今年1月,京東上Kindle大面積缺貨現象引發熱議,另有傳言稱,Kindle可能要退出中國市場。記者在電商平臺檢索發現,亞馬遜Kindle天貓官方旗艦店已于2021年10月底閉店,至今未恢復。京東自營旗艦店上,除了一款低端型號外,Kindle產品均顯示無貨。
另據《新京報》援引亞馬遜中國內部多個獨立信源的消息,公司Kindle硬件團隊已于去年11月被裁撤。6月2日,Kindle方面同時表示,在2022年1月以后購買的Kindle電子書閱讀器,可以申請退貨。
自2013年6月7日首現于中國市場,Kindle進入中國已經9年了。曾經被一眾精英人士所推崇,并改變了很多人的閱讀習慣。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閱讀器賽道上,Kindle已不再獨領風騷,小米、掌閱、科大訊飛等一眾國內品牌已在市場上嶄露頭角。
反觀Kindle,則已從精英人士擁躉的“閱讀神器”淪落為屌絲的“泡面神器”。巨大的落差,讓人疑竇叢生:這9年,到底發生了什么?誰動了Kindle的奶酪?
一、為進入中國,曾用盡“渾身解數”
多數人買Kindle,是為了讀書,但買了之后才發現:購買Kindle,并不等于讀書。肖力曾買過兩款不同型號的Kindle,相隔僅一年時間,但兩款Kindle的結局都是“轉送他人”。
肖力2017年3月入手了第一款Kindle——Paper white3,滿懷憧憬地希望它成為自己的“閱讀神器”,助力自己“破萬卷書”。然而,用了不到5個月,因其“屏幕太小,反應太慢,標注起來很麻煩”,就懶得再用了。正好,小姨來家里玩,就轉贈給了她。
與Paper white3分別4個月后,不堪忍受“不讀書的日子”,肖力又入手了一款屏幕尺寸較大的Kindle。新鮮勁兒一過,電子書閱讀的厭倦感再次泛起。事實證明,Kindle的確不是他的“菜”。
“這是一款很‘笨’的商品,不像iPad那么精致漂亮。的確有人用得很好,但對我來說,閱讀的話,有錢還是買書吧,最直接也最方便,涂涂畫畫直接用筆就行,還不用忍受‘殘影’,除了搬家費點兒勁。”
用了沒多長時間,這款Kindle在“吃灰”的第三個月被肖力送人了。

被肖力兩度“拋棄”的Kindle,那時進入中國市場剛幾年時間。2013年6月7日,是Kindle進入中國的第一天,在此之前,很多中國網友曾在各類貼吧、論壇里翹首以待,呼吁Kindle進入中國。
為進入中國,亞馬遜和貝索斯早有布局。
早在2010年7月,就有媒體發現,亞馬遜已經在北京開始招募Kindle供應商管理的相關崗位,引發關于Kindle即將進入中國的討論。但9月,貝索斯通過亞馬遜官方回應稱,Kindle閱讀器和相應的內容都沒有進入中國,希望未來會有所計劃。
到了2011年下半年,亞馬遜前往拜訪中國最大的商業圖書出版公司——中信出版社。他們介紹了團隊、觀念、商業模式,并主動了解中信的情況;在華銷售沒幾天后,時任亞馬遜中國副總裁白駒逸就去拜訪商務印書館管理層,商談版權合作事宜。
那時商務印書館數字出版中心主任孫述學評價稱:“白駒逸對中國的事情比較了解,本土化工作做得還可以。”
在Kindle進入中國之前,以漢王為首的電子書閱讀器生產商一直將其當做是一款“奢侈品”,2004年前后,漢王產品的毛利率高達50%-60%,是聯想等電腦廠商的3-4倍。但當Kindle進入中國之后,貝索斯的低價甚至虧本甩賣硬件策略,直接近乎壓垮了漢王等一干國內硬件生產商。到了2013年,漢王的毛利率已經只有10%左右。
這背后自然依賴于亞馬遜平臺的助推,在2010年前后,亞馬遜就已經有了超過60萬種電子書、雜志以及博客訂閱,同時,又要求國內出版商在Kindle渠道給出最低價格的定價,吸引中國讀者的關注。
除了正規版權和低價策略,亞馬遜也從Kindle的功能和文化屬性上,努力開拓中國市場,適應中國讀者。
功能上,2014年,Kindle推出了對英文生詞提示功能,并支持筆記分享微信或微博,以此提高用戶體驗;2017年,亞馬遜與當時的網絡文學大平臺咪咕閱讀合作,推出定制版Kindle X,包含Kindle閱讀和咪咕閱讀兩個系統,以此改變自身“深度閱讀工具”的固有形象。
文化上,亞馬遜中國曾以其他消費電子產品舉例,向美國總部證明白色很受中國用戶歡迎。2015年3月,白色Kindle在中國上市后受到追捧,也印證了這一舉措的正確性;后來,亞馬遜又一改單調配色,以中國傳統顏料為靈感,推出霧藍、煙紫、玉青等多配色產品。此外,2018年,亞馬遜還和故宮合作,推出故宮文化版電子閱讀器。


亞馬遜的努力,的確沒有白費,Kindle曾一時風光無二。
數據顯示,2013年到2018年,Kindle電子閱讀器在中國已累計銷售數百萬臺;中國成為亞馬遜全球Kindle設備銷售第一大市場;Kindle中國電子書店的書籍總量近70萬冊,較2013年增長近10倍。
而且,隨著Kindle上中文書籍銷量上升,出版社和亞馬遜的角色也發生了微妙變化:以前是亞馬遜找出版社,后來變成出版社請亞馬遜助推新書。在亞馬遜網站上,曾有作者和出版機構為了自己作品拿到好評絞盡腦汁,更有作者直接將自己的作品在亞馬遜上一舉走紅,完全不再看出版社和零售商的臉色。

2015年4月,亞馬遜Kindle《冰與火之歌》造型亮相北京王府井步行街。
二、左手泡面,右手吃灰
一時領先,不代表始終領先。Kindle仿佛一粒石子,激起了中國閱讀器大市場的浪花,但自己卻要被這浪花淹沒了。
“泡面神器”,恐怕是Kindle的第一次“出圈”。
2019年3月,亞馬遜官微推出了一則廣告文案,一部Kindle被蓋在一盒泡面上面,旁邊的文字顯示“蓋Kindle,面更香”。甚至用Kindle自帶的時鐘功能設置了“倒計時5min”。

這波帶著“自黑”范兒的營銷,著實在當時引起了轟動。除了網友紛紛跟風高呼“腦洞大開”之外,更有人專門拿出三部不同型號的Kindle和三碗不同口味的泡面,一本正經地在網上做起了“哪款Kindle蓋的面最香”的視頻。
如今回過頭來看,Kindle的這波自黑式營銷竟變成了現實,用戶真的覺得用Kindle泡面比讀書更實用。Kindle的本質想法,是讓讀者在更多的場景中拿起Kindle。反諷的是,2018年就有網友發帖表示,Kindle已經成為自己手里的各大數碼產品中,“吃灰”最多的那部。
首要原因是,Kindle“不耐用”。
以閱讀功能切入市場的Kindle,采用的是黑白電子墨水屏幕。這款屏幕的優點是低功耗續航時間長,同時最大限度降低對眼睛的壓力,屏幕顯示完全依據電壓來驅動,屏幕本身并不發光,是所有電子產品中最接近紙張的,也是最接近紙質書閱讀體驗的。
但這類屏幕實在“太過金貴”,一款屏幕的價格近乎相當于半個Kindle的價格。而且屏幕一旦受到一點點的磕碰,就會留下無法修復的光斑。此外,還有不可避免的閃屏、跳屏的問題,使得Kindle只要出現一點點損傷,大多數用戶就會自動將它扔到角落里“吃灰”。
憑借低價策略短暫地獨領風騷后的Kindle,很快遇到了國產閱讀器的新一波崛起,并且“花式創新”。
先看國產。掌閱和科大訊飛在2020年同一天推出了全球首款彩色墨水屏閱讀器,對于很多閱讀器使用者來說,這可是一大福音:閱讀圖片圖表終于不再受黑白屏的困擾;屏幕尺寸也有了更多選擇:5.84英寸的海信A5可以像手機那樣解鎖更多使用場景;7.8英寸的小米多看,兼顧了輕便和大屏;10.3、13.3英寸的文石閱讀器更加方便了無紙化的辦公。

左為科大訊飛C1彩屏閱讀器,右為掌閱C6 pro彩色墨水屏閱讀器
再看Kindle。2015年,KPW3發布,相比KPW2,除了CPU外,屏幕分辨率有了巨大提升;到了2018年,KPW4發布,僅外形做了更新,更加防水,此外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2021年9月,KPW5發布。亞馬遜似乎聽到了廣大用戶的心聲:USB-C接口出現,屏幕尺寸也從上一代的6英寸上升到了6.8英寸。但這種“小打小鬧”“不夠刺激”的變化很難觸動中國消費者的神經。正如網友留言:“泡面蓋得更嚴實了”“半年后,閑魚見”。

當別人都變,Kindle不變時,它很難繼續是必選或首選項。

有用戶一語戳中當下Kindle的尷尬境地:“很多人購買Kindle并不是為了讀書,只是一種為了滿足‘我有在讀書哦’的自我安慰劑。”
另一個原因是Kindle自身功能的單一。隨著智能手機、Pad以豐富的功能占據電子產品市場,融合了社交、視頻、拍照、閱讀、導航等多功能的電子產品更加受到用戶的青睞。而很多有專業閱讀需求的用戶,如考研的學生、教授等更傾向于使用iPad,更大的屏幕,更快的刷新率,更豐富的筆記軟件,更簡單的pdf導入,更豐富的圖書資源。這對Kindle來說,無疑是一個強勁對手。
記者對比發現,一個基礎款最新iPad在京東的售價是2499元,而如果選擇購買前一年的老款或者選擇購買二手iPad價格會更低。而京東上Kindle 最新的旗艦款OASIS3 的售價為2899,價格完全足夠買一個基礎款的iPad。
“有朋友曾給自家侄子送了一部Kindle和一部iPad,等到過年回家之后,看見侄子抱著iPad在玩游戲,Kindle早就不知道撇哪里去了。”有用戶如是表示。
三、劉強東一語成讖
從2007年亞馬遜推出第一代Kindle,到現在的Paperwhite、oasis等系列產品,伴隨著時代的發展,Kindle已經走過了15個年頭。最先被Kindle改變的,是中國年輕人的閱讀習慣。
高晨是Kindle的一名忠實用戶,她使用Kindle將近兩年半的時間。“我現在紙質書看得少了,以前一個月大概能看1-2本,但是買了Kindle之后,紙質書幾乎不怎么看了,”高晨說,“Kindle使用起來很方便,乘坐火車時可以隨身攜帶,隨時隨地享受閱讀時光,睡覺之前也可以用來看看書,不用一直依賴手機,有利于養成良好的習慣。”
2020年度中國數字閱讀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數字閱讀用戶規模達4.94億,增長率達5.56%,人均電子書閱讀量9.1本。與此相對的是,人均紙質書閱讀量6.2本,同比上一年減少2.6本。
不過,微博、短視頻和智能手機的出現,使得Kindle無論在內容生態上,還是終端應用價值上,又很快被用戶所忽略,直至瀕臨淘汰出局。“Kindle使用起來沉浸感較差,我有時難免被外界的其他聲音所干擾。”高晨說。
另有曾經的Kindle用戶告訴記者:“現在的短視頻太吸引人了,每天打開抖音都停不下來,微博上的熱搜更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晚上躺到床上時,我只想刷刷微博、抖音,買回來的Kindle擱在家里一角,仿佛就是個裝飾品,只是偶爾打開看一看。”
Kindle作為電子閱讀的載體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數字閱讀的發展。一直以來,亞馬遜以圖書業務作為切入口,以Kindle電子書店和系列產品為基礎,構建Kindle生態圈,亞馬遜與傳統出版業的合作一直是數字內容產業盈利模式的典范。
但是,亞馬遜搭建的內容生態,和出版社幾經周折談下來的合作,如今又受到短視頻的沖擊,被移動端的休閑方式消磨。用戶拿來讀書的時間和耐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據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截至2021年6月,短視頻用戶規模達8.8億人,相當于中國網民規模的87.8%,短視頻正在成為全民最熱的休閑方式。
不僅如此,亞馬遜自身在中國的處境也并不樂觀。2021年4月,亞馬遜一波“向5萬中國賣家宣戰”的消息引發輿論熱議,彼時,大量中國賣家遭遇亞馬遜的“封店”處理,理由與賣家刷好評有關。
很難說這波操作究竟誰是誰非,但亞馬遜此舉顯然讓自己在中國市場上受損不少。在“宣戰”風波之后,肖力還動過入手閱讀器的想法,但在長時間對比多家產品后,他還是放棄了。
肖力最終得出結論:“與其糾結閱讀器,我為什么不買個iPad,什么資源都能看。”“所謂沉浸式閱讀很有bug,不愛讀書的,給他啥他也看不下去,與硬件導致的‘分心’關系不大。”
“亞馬遜的Kindle在中國是絕對沒法做成功的。”十多年前,電商大佬劉強東曾這樣預言。如今,這個預言已然成真。

作者公眾號:鳳凰WEEKLY財經(ID:fhzkzk)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范轉載侵權必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授權事宜請至數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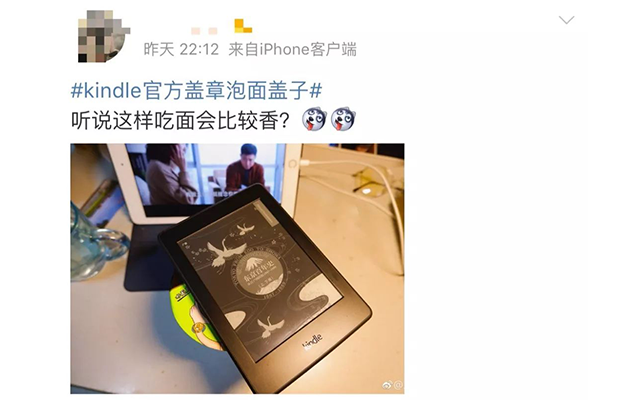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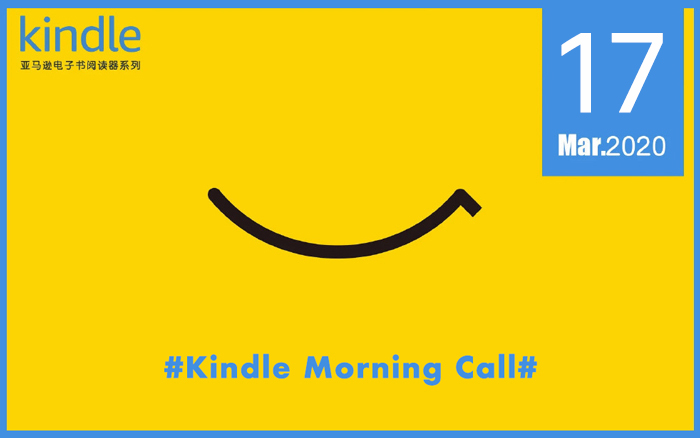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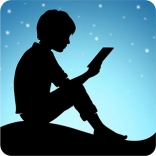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全部評論(15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