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卻迷人:五條人的媒介形象是如何被建構(gòu)起來的?
首發(fā):全媒派
人字拖、花襯衫、皮夾克、黑墨鏡,憑借自身獨(dú)有的魅力,一個(gè)名為“五條人”的樂隊(duì)組合迅速走紅。這支來自南方小城海豐的樂隊(duì),在《樂隊(duì)的夏天》節(jié)目中臨場(chǎng)換歌、猜拳耍賴、插科打諢,雖然制造了如此多的意外,他們的出格行為卻為節(jié)目帶來了強(qiáng)烈的戲劇效果。
于是,在短短的時(shí)間內(nèi),這支原本只在小眾圈層有一定知名度的樂隊(duì)成功出圈,成為了主流媒體的采訪對(duì)象,也為自媒體提供了創(chuàng)作素材,人們追溯他們的來路,企圖為他們今天引人注目的表現(xiàn)做出一些解釋與說明。于是,一個(gè)特立獨(dú)行、雖然市井卻不乏知識(shí)分子氣質(zhì)的樂隊(duì)形象迅速被媒體建構(gòu)起來。本文聚焦該樂隊(duì)的突然流行,探討媒介傳播在塑造五條人形象特質(zhì)上發(fā)揮的作用以及社會(huì)鏡頭中的五條人如何被消費(fèi)的。
媒介放大與可見性:五條人屬于互聯(lián)網(wǎng)
這次五條人能夠引發(fā)如此多的討論,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綜藝節(jié)目的推介作用,其增大了樂隊(duì)文化的可見性,并把爭(zhēng)議問題擺到臺(tái)前,成為大眾的討論對(duì)象。早期的五條人樂隊(duì),雖然沒有太多的媒體曝光資源,但他們也對(duì)媒體的邀約保持警惕,曾經(jīng)多次拒絕電視節(jié)目的邀請(qǐng)。
可以說,大紅大紫的五條人,是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的產(chǎn)物,而不屬于電視時(shí)代。電視這一視聽媒介并不像互聯(lián)網(wǎng)流媒體那樣帶有強(qiáng)烈的去中心化屬性,互聯(lián)網(wǎng)作為一種不同于傳統(tǒng)媒介的 “高維媒介”,其最大的特點(diǎn)是改變了以往以“機(jī)構(gòu)”為基本單位的傳播格局,取而代之的是以“個(gè)人”為基本單位的社會(huì)傳播。
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更有利于像五條人這樣的樂隊(duì)的形象建構(gòu)。一方面,參加擁有高社會(huì)知名度的節(jié)目,為五條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媒介可見性。作為一種知識(shí)隱喻和社會(huì)過程,可見性這一概念在性別研究、少數(shù)群體研究、傳播研究和社會(huì)權(quán)力研究當(dāng)中都被認(rèn)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基于“看”的認(rèn)識(shí)論,社會(huì)意義上的“可見性”是一種承認(rèn),而承認(rèn)則是理解人類身份的基本類別,這對(duì)于洞見少數(shù)群體與主流之間的關(guān)系至關(guān)重要。
中國(guó)國(guó)內(nèi)與五條人相似的樂隊(duì)也并不是沒有,如四川的白水、福建的老街、西北的蘇陽(yáng),但他們卻并沒有像五條人一樣獲得這么大的關(guān)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yàn)樗鼈儧]有獲得更多的媒介可見性。另一方面,跟《樂隊(duì)的夏天》上一季中與五條人類似的黑撒樂隊(duì)、九連真人相比,五條人似乎比他們?cè)诨ヂ?lián)網(wǎng)世界擁有更多的討論量。
這或許是因?yàn)槲鍡l人自身承載的種種反差性,迎合了泛娛樂化的互聯(lián)網(wǎng)語(yǔ)境,五條人幽默詼諧的話語(yǔ)與渾不吝的各種姿態(tài),為網(wǎng)友提供了造梗的素材來源。甚至可以說,現(xiàn)在很多人關(guān)注到五條人,并不是因?yàn)樗麄兊母枨撬麄兩l(fā)出的種種趣談與段子。
人們也許對(duì)五條人唱什么歌不感興趣,只是在意此刻出現(xiàn)的五條人所帶來的反差感。這些梗、趣談與段子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獲得大量傳播,一個(gè)痞氣十足、不守規(guī)則的樂隊(duì)形象就這樣被建構(gòu)起來。這也就是李普曼所說的擬態(tài)環(huán)境,一種在各種信息作用下所建構(gòu)的媒介環(huán)境,這是有別于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的擬態(tài)化世界。

圖源:微博@五條人樂隊(duì)WUTIAOREN
歌詞文本與聲音特質(zhì):五條人的呈現(xiàn)與表達(dá)
離開單一的對(duì)互聯(lián)網(wǎng)所建構(gòu)擬態(tài)環(huán)境的探討,我們或許可以發(fā)現(xiàn)其他媒介環(huán)境中五條人形象的建構(gòu)過程。
在“作者已死”的年代,評(píng)價(jià)者往往對(duì)創(chuàng)作者有更大的解讀主動(dòng)權(quán)。現(xiàn)代音樂曲量多樣繁雜,作為相關(guān)延伸職業(yè)的樂評(píng)人則牢牢把握著評(píng)價(jià)音樂人的話語(yǔ)權(quán)。以往音樂人對(duì)于五條人音樂的評(píng)價(jià)往往集中在五條人歌詞的文本層面,人們認(rèn)為來自底層的五條人有自我書寫、自我歌唱的能力與勇氣,稱贊他們是來自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的知識(shí)分子,他們甚至比那些藏于書閣進(jìn)行寫作的知識(shí)分子具有更廣闊的書寫對(duì)象與更鮮活的表達(dá)方式。
例如,他們既觸及歷史,講述亂世英雄或亂臣賊子的故事;也觸達(dá)現(xiàn)實(shí),將那些就圍繞在他們身邊的人都作為歌唱對(duì)象——賣CD的街邊小販,樸素的穿拖鞋跳舞的姑娘,可以代表無數(shù)普通男女的阿強(qiáng)與阿珍;他們也是民俗文化的發(fā)掘者,有關(guān)海豐的祭祖?zhèn)鹘y(tǒng),他們就創(chuàng)作了《清明過紙》與《請(qǐng)到老祖宗》兩首歌曲,有了海豐白字戲的加入也使得《像將軍一樣喝酒》錦上添花;他們甚至還是公共議題的發(fā)聲者,許許多多社會(huì)新聞都成為了他們歌曲的素材乃至主體敘事部分,連全球化退潮的世界樣態(tài)也要被他們戲耍一番……
這一系列勇敢的歌唱讓專業(yè)樂評(píng)人歡欣不已,他們驚嘆這支樂隊(duì)的出現(xiàn)。樂評(píng)人馬世芳感慨五條人的專輯《一些風(fēng)景》是他等了20年的唱片,而樂評(píng)人張曉舟甚至把他們比作本雅明筆下波德萊爾那樣的城市漫游者,認(rèn)為他們即使是混跡于流浪漢和爛仔之間,卻依然清楚自己是個(gè)“文化人”。

圖源:@樂隊(duì)的夏天
這些樂評(píng)人的贊美之詞為我們建構(gòu)了一個(gè)具有強(qiáng)烈人文關(guān)懷的五條人形象,這些樂評(píng)人對(duì)他們的評(píng)價(jià)被后來者不斷引用,即便真實(shí)的五條人并不承認(rèn)這些靜止化的標(biāo)簽與定義。
當(dāng)然我們并不否定樂評(píng)人基于五條人歌曲文本層面作出的評(píng)價(jià)與解讀,但是不同的表達(dá)者往往要借助不同的媒介。對(duì)于音樂人來說,樂器就是他們表達(dá)的媒介,音樂作品就是塑造自身媒介形象的第一中介物。樂評(píng)人所犯的錯(cuò)誤就是他們往往忽視了五條人歌曲的非文本層面,忽視了五條人歌曲中由聲音所營(yíng)造的空間,以及這種聲音空間與聽眾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從而放棄了從聲音的維度上來討論五條人的可能性。這也是我們聽音樂總被樂評(píng)人牽著鼻子走的重要原因。
聲音不僅僅承載著信息,同樣有其音色、音量、音調(diào)等等。聲音是一種媒介,它中介了人與人、人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既是人感受周圍世界的一種尺度,也是人涉入世界的一種方式。因此,如果暫時(shí)忘記樂評(píng)人帶給我們的二手解讀,可能會(huì)看到五條人更真實(shí)的自我建構(gòu)。
我們也可以在五條人的歌曲中發(fā)現(xiàn)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世界。突然闖入的汽笛聲,自行車的腳鏈聲,城中村的雜音,凄厲尖銳的豬叫聲,小鎮(zhèn)鐵鋪的敲打聲,喧鬧集市里的自行車鈴聲,阿媽的念叨聲,一切聲音都可以在五條人的歌曲中找到,這些自然而然的具有生命力的聲響,從聽覺的維度上建構(gòu)了一個(gè)具有現(xiàn)實(shí)主義特質(zhì)的五條人形象。
精致的粗糲:五條人的視覺美學(xué)
五條人在外人看來充滿反差感,這種反差感既體現(xiàn)在玩世不恭上,也體現(xiàn)在五條人自身的矛盾性上。這種矛盾性很多時(shí)候來自于人們的刻板印象,認(rèn)為不羈隨意的五條人應(yīng)該沒什么文化,可他們卻恰恰與之相反,別有一種知識(shí)分子的內(nèi)在底蘊(yùn)。他們的歌詞甚至被刊登在文學(xué)期刊上,并被評(píng)論者稱贊具有較高的文學(xué)價(jià)值。
打破常規(guī),跳出所有人的期待,就是五條人的特質(zhì)。而優(yōu)秀的視覺設(shè)計(jì)會(huì)讓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主體接近其藝術(shù)表達(dá)的本質(zhì)。整體來說,建構(gòu)五條人的不只是節(jié)目剪輯、媒體采訪、他們的歌曲以及樂評(píng)人對(duì)他們的評(píng)價(jià),包括海報(bào)、服裝、外形以及種種都在塑造著這個(gè)樂隊(duì)的整體形象。

圖源:五條人士多店
所以從根本上說,五條人選擇了另一種建構(gòu)自身形象的方式,即依托自身的創(chuàng)作語(yǔ)境展開豐富的視覺表達(dá)。這種視覺表達(dá)集中體現(xiàn)在五條人專輯封面與演出海報(bào)的設(shè)計(jì)上。
主唱仁科在離開海豐之前,曾在工藝美術(shù)班學(xué)過畫畫,也曾在貝雕廠工作,為貝殼畫畫,所以他本身就具有較高的審美素養(yǎng)與美學(xué)功底。[6]另一方面,從2012年起,五條人就有了自己的御用設(shè)計(jì)師,這位名叫胡鎮(zhèn)超的專業(yè)設(shè)計(jì)師科班出身,一直從事平面設(shè)計(jì)工作,并是五條人最早的一批歌迷之一。他與五條人保持良好的合作關(guān)系,作為歌迷的他精準(zhǔn)了把握了不同時(shí)期五條人的風(fēng)格特點(diǎn)。
當(dāng)五條人還處在歌唱“懷舊”與“流浪”的階段,設(shè)計(jì)師胡鎮(zhèn)超不停去發(fā)現(xiàn)與五條人的音樂和縣城息息相關(guān)的事物,同時(shí)從自身的生活環(huán)境去尋找靈感,比如夏天乘涼用的扇子,或是海豐縣街頭的三輪車,并想辦法嘗試了不同的表現(xiàn)手法,如攝影、木刻、拼貼等,在海報(bào)中突出拖鞋或是編織袋這類從側(cè)面代表縣城青年的元素。

圖源:胡子設(shè)計(jì)工作室
更為重要的是,經(jīng)過專業(yè)美學(xué)訓(xùn)練的胡鎮(zhèn)超為五條人注入了更多現(xiàn)代性因素。拼貼解構(gòu)、觀念攝影、涂鴉符號(hào)、圖形變異等各種現(xiàn)代設(shè)計(jì)方法都統(tǒng)統(tǒng)被胡鎮(zhèn)超運(yùn)用到了設(shè)計(jì)中,“回到海豐”演唱會(huì)海報(bào)中,用瓜子、花生拼出來的吉他,gif動(dòng)畫中在海上從風(fēng)扇出來的海風(fēng),從海豐白字戲戲臺(tái)背景汲取靈感設(shè)計(jì)的威風(fēng)老虎,這種從細(xì)節(jié)上建構(gòu)的五條人形象直擊人心。
從這個(gè)意義上講,胡鎮(zhèn)超是五條人視覺形象的成功建構(gòu)者,因?yàn)樗韧ㄟ^視覺設(shè)計(jì)傳達(dá)了五條人本身就具有的豐富精神,同時(shí)也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五條人的本來特質(zhì),實(shí)現(xiàn)了一種更高層次上的五條人美學(xué)的建構(gòu),即通往一種現(xiàn)代審美的五條人美學(xué),一種屬于五條人的“精致的粗糲”,一種屬于五條人的“縣城美學(xué)”。精致而充滿表現(xiàn)力的視覺設(shè)計(jì),證明著五條人并不土,反而是一種美學(xué)現(xiàn)代性的存在,這種美學(xué)現(xiàn)代性自成體系,市井卻不頹廢,以自我啟蒙完成全部書寫與價(jià)值表達(dá)。
突然被凝視的命運(yùn):成為文化消費(fèi)符號(hào)
與大多數(shù)流行偶像每天更新不斷的物料相比,五條人在互聯(lián)網(wǎng)中擁有的圖片或影像資料并不多,但這對(duì)于該樂隊(duì)來說已經(jīng)足夠了,因?yàn)檫@同樣是五條人反類型化風(fēng)格的體現(xiàn)。對(duì)于神秘的五條人來說,尋找他們過去的存在痕跡就像在進(jìn)行一次又一次艱辛的考古,但一旦有所發(fā)現(xiàn),那便是勾連今日五條人的珍貴文本。
與其說五條人是反流行文化的,不如說他們不配合的獨(dú)立姿態(tài)亦成另一種流行文化的風(fēng)格,而這種風(fēng)格在娛樂市場(chǎng)缺失已久,且被大眾期待。所以五條人受到如此多突如其來的歡迎,也側(cè)面說明,縱使作為文化工業(yè)精心打造的偶像明星擁有著巨大的受眾,那被排除在繁榮飯圈以外的其他人也始終在等待一個(gè)屬于他們的“偶像”,而“寧愿土到掉渣,也不愿俗不可耐”的五條人的出現(xiàn),則剛好填補(bǔ)了一點(diǎn)空白。

圖源:五條人士多店
當(dāng)種種復(fù)雜因素相互疊加,各種外部聲音對(duì)五條人進(jìn)行了無比細(xì)致的形象建構(gòu),真正的五條人在這一刻也漸趨退場(chǎng),被毫不留情地裹挾進(jìn)消費(fèi)主義的漩渦。他們是市場(chǎng)空缺已久的人設(shè)類型,他們成為一種代表另類風(fēng)格的文化消費(fèi)符號(hào)。自8月底節(jié)目播出后,五條人獲得的關(guān)注度不斷升高,先后接受了多家媒體的采訪,也成為李佳琦直播間的座上客,各種標(biāo)簽蜂擁而至,即使五條人一再?gòu)?qiáng)調(diào)自身的變化性,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外界的評(píng)價(jià)無所謂,但是他們并沒有意識(shí)到,定義他們自己身份的權(quán)力早已不在他們手中。
互聯(lián)網(wǎng)是一個(gè)場(chǎng)域,這個(gè)場(chǎng)域有著自身運(yùn)行的規(guī)則,占據(jù)相應(yīng)位置的個(gè)體、群體或機(jī)構(gòu)掌握著不同的資本,各種各樣的資本擁有者彼此競(jìng)爭(zhēng),以求自己擁有的資本能取得支配的地位。作為新入場(chǎng)者,縱使做出種種破壞規(guī)則的行動(dòng),可一旦入局,五條人就不可避免地迎來了被誤讀、被收編的命運(yùn)。于是,五條人成為了營(yíng)銷對(duì)象,在文化工業(yè)以消費(fèi)文化為主導(dǎo)的運(yùn)作邏輯下,五條人的某些屬性被有意突出,而有些屬性則被有意遮蔽,五條人獲得了一種“反人設(shè)”的人設(shè)。于是,他們的不守規(guī)則反而給節(jié)目制造了意外的效果,“撈五條人”也成為了一種行為藝術(shù)式的狂歡,他們所有一切的反抗依然沿著資本設(shè)定好的方向被流量的風(fēng)暴平靜地裹挾著。
也許,悲觀地看,五條人終究會(huì)成為被眾人凝視的對(duì)象,現(xiàn)在的一切表現(xiàn)都會(huì)被誤讀并再次納入那個(gè)“反人設(shè)”的媒介形象,即使真實(shí)世界中的他們并不這樣,但這些早已無關(guān)緊要。由此帶來的狂歡與圍觀簇?fù)碇鍡l人,直到淹沒他們。
當(dāng)然,揭示五條人運(yùn)作背后的消費(fèi)主義邏輯并不代表我們對(duì)資本持完全批判的態(tài)度。正是有了資本的加持,五條人樂隊(duì)才不至于呈現(xiàn)為極度的粗鄙化,而能夠找到雅與俗的中間點(diǎn)與市場(chǎng)的最大公約數(shù),借助商業(yè)給予的專業(yè)資源,達(dá)成自身特質(zhì)的最佳風(fēng)格化與音樂作品的優(yōu)質(zhì)生產(chǎn)。我們自然不必過分惋惜,在更大意義上,對(duì)于亞文化而言,正是這種張力,激發(fā)了一代又一代行動(dòng)者,促進(jìn)著我們文化生態(tài)的持續(xù)建構(gòu)與生長(zhǎng)。
參考鏈接:
1.喻國(guó)明.互聯(lián)網(wǎng)是高維媒介:一種社會(huì)傳播構(gòu)造的全新范式——關(guān)于現(xiàn)階段傳媒發(fā)展若干理論與實(shí)踐問題的辨正[J].編輯學(xué)刊,2015(04):6-12.
2.陸曄,賴楚謠.短視頻平臺(tái)上的職業(yè)可見性:以抖音為個(gè)案[J].國(guó)際新聞界,2020,42(06):23-39.
3.https://mp.weixin.qq.com/s/hDIW4UTbAYF034MzUV9Bfw
4.https://site.douban.com/wutiaoren/widget/notes/412234/note/280938576/
5.季凌霄.從“聲景”思考傳播:聲音、空間與聽覺感官文化[J].國(guó)際新聞界,2019,41(03):24-41.
6.https://mp.weixin.qq.com/s/A9znfcnKLeNdLx8yKL0bjg
7.https://mp.weixin.qq.com/s/hJbIR0nookMgMTcj_z9mYQ
8.https://mp.weixin.qq.com/s/TWk0aSbQ7O7GzSDz068Qow
作者:高涔朝
作者公眾號(hào):全媒派(ID:quanmeipai)
轉(zhuǎn)載請(qǐng)?jiān)谖恼麻_頭和結(jié)尾顯眼處標(biāo)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未經(jīng)授權(quán)嚴(yán)禁轉(zhuǎn)載,授權(quán)事宜請(qǐng)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quán)必究。
本文禁止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授權(quán)事宜請(qǐng)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hào)(ID: digitaling) 后臺(tái)授權(quán),侵權(quán)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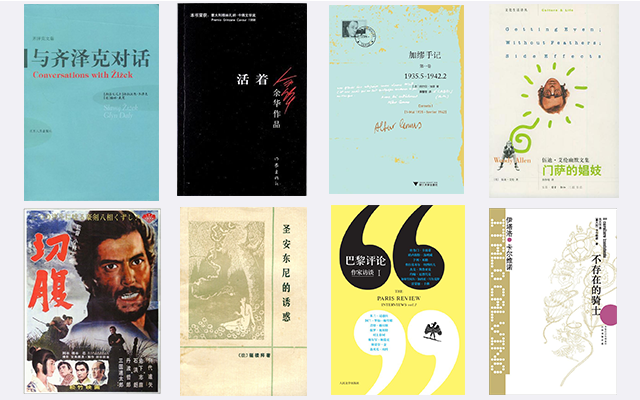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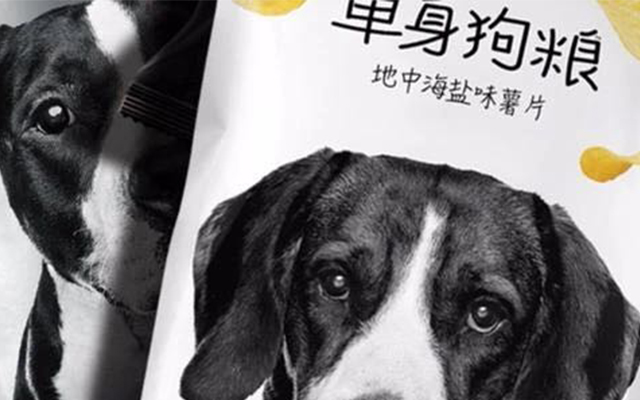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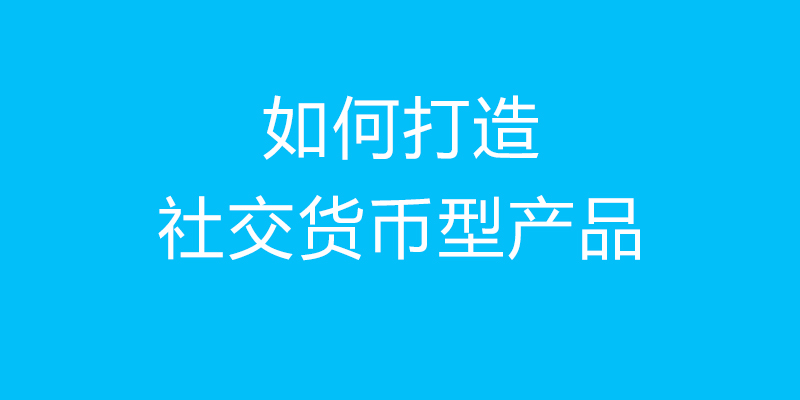



評(píng)論
評(píng)論
推薦評(píng)論
全部評(píng)論(1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