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作家許知遠(yuǎn):43歲,我意識到自己沒那么重要

這是紅沙發(fā)專訪的第15期。
7月初一個(gè)星期三的午后,在北京東四環(huán)外的單向空間書店二層,我見到了許知遠(yuǎn)。
專訪許知遠(yuǎn)的念頭由來已久。如同他以主持人身份在談話節(jié)目《十三邀》里好奇每個(gè)獨(dú)特個(gè)體自身的經(jīng)驗(yàn),以及TA們與這個(gè)時(shí)代、與整個(gè)公共話語空間的相處之道,我也好奇他在短暫節(jié)目之外、在爭議“網(wǎng)紅”之下的真實(shí)故事,和他與這時(shí)代的談話內(nèi)容。
兩個(gè)月前,許知遠(yuǎn)歷時(shí)五年時(shí)間著成的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以下簡稱《青年變革者》)正式出版。以“作家歸來”的姿態(tài),許知遠(yuǎn)再次出現(xiàn)在大眾視野中,也是他時(shí)隔八年再次在中國大陸成功出版書籍。它促使了我下決心正式向他發(fā)出專訪的邀請(很感謝他能接受Flipboard紅板報(bào)的專訪),也將我的好奇推向了另一維度:“作家”這一身份對他是否是一種執(zhí)著。

不算寬敞的辦公室,環(huán)繞四壁的書架和一張靠窗的長桌上,擺滿了書。多是文學(xué)、歷史書籍,穿插著人物傳記。匆匆對付了同事準(zhǔn)備的午餐,許知遠(yuǎn)坐在沙發(fā)里,有些疲倦。
剛剛過去的周末,他奔赴鄭州、武漢、長沙三地,參加《青年變革者》新書分享會,與當(dāng)?shù)氐淖x者粉絲見面。專訪的前一天,《十三邀》第四季錄制,9個(gè)小時(shí)的拍攝,他忙到深夜。如此密集而匆忙的行程,許知遠(yuǎn)早已適應(yīng)。自2016年開始做《十三邀》起,許知遠(yuǎn)就發(fā)現(xiàn)自己的時(shí)間需要精打細(xì)算——一檔談話節(jié)目的主持人、一家書店的管理者、三檔播客節(jié)目的主持人、一本《青年變革者》的執(zhí)筆人,這是過去三年時(shí)間里,許知遠(yuǎn)忙碌的所有事務(wù)。
他現(xiàn)在“學(xué)會”了一種“交替式”的休息方式。“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書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shí)候,就去管理公司。”許知遠(yuǎn)不太有時(shí)間管理自己的公司,“他們都說,(我)管理得很糟”。
單向空間花家地店未搬遷之前,許知遠(yuǎn)喜歡在那里工作,他會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店里,一待就是一整天。最近這段時(shí)間,這樣大把的空閑時(shí)間,對他來說是奢望。同一家公司的單讀同事想要在辦公室里攔住他采訪幾個(gè)問題,也需要一周碰一次運(yùn)氣。
在長沙,時(shí)務(wù)學(xué)堂舊址,72歲陳書良老先生用長沙話吟誦梁啟超的詩。這是對許知遠(yuǎn)來說,忙碌行程中為數(shù)不多的欣慰之處。在北京的新書首發(fā)儀式上,類似的場景是,不同地域的年輕人用當(dāng)?shù)氐姆窖岳首x《青年變革者》的片段,新會、廣州、長沙、北京、上海、天津......每一個(gè)城市都是梁啟超56年生命旅途中的重要站點(diǎn)。
許知遠(yuǎn)說,這是他的主意。“我期待聽到他們對書的理解,這對我來說是有意思的。坦白說,新書的各種活動不是為了我自己,甚至也不是為了出版社。本質(zhì)上真的希望梁啟超這個(gè)人,他的經(jīng)歷,他的故事能夠被更多年輕人去知道和理解。”許知遠(yuǎn)認(rèn)為他有一份責(zé)任,是讓梁啟超的遺產(chǎn),在其逝世90年后的今天得到某種程度的復(fù)活。

許知遠(yuǎn)在新書首發(fā)式上
《青年變革者》正式提筆于2015年底,寫成于2018年夏天,近一年時(shí)間后期編輯才出版面世,許知遠(yuǎn)坦言“他已經(jīng)對這本書失去了激情”。“我有嗜新癥。容易厭倦,老是期望被suprise(驚奇)”,末了,他自嘲地補(bǔ)充道,“可能心理比較幼稚吧,小孩才需要驚奇感”。
但或許也正因?yàn)槿绱耍?00多年前,那個(gè)歷史書上僅三言兩語描繪的梁啟超和他所處的時(shí)代,才有足夠的新奇和魅力吸引到許知遠(yuǎn),并驅(qū)使他去完成梁啟超傳記三卷本。不止一次地,許知遠(yuǎn)表達(dá)過,他希望這三卷本的傳記成為一部悲喜劇、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我期望它能復(fù)活時(shí)代的細(xì)節(jié)與情緒,展現(xiàn)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
很難講,許知遠(yuǎn)沒有把個(gè)人對眼前這個(gè)巨大轉(zhuǎn)折年代的擔(dān)憂與期待,投射到《青年變革者》這本書之中去。“這么復(fù)雜的世界,你所有的情感在那個(gè)歷史世界都會找到投射,都會找到印證。”投射之后找到當(dāng)初疑惑問題的答案了嗎?許知遠(yuǎn)笑著說道,“還在找。如果答案找到了,后半生都虛無了。肯定在繼續(xù)找,這是一個(gè)一直的過程。”
但至少,許知遠(yuǎn)找到了其中一個(gè)答案——作家身份的回歸。當(dāng)被問及“是否有身份上的焦慮?”——這是《十三邀》里,許知遠(yuǎn)最常向采訪對象提出的一個(gè)問題,許知遠(yuǎn)沉默思考了很長一段時(shí)間。“有吧。現(xiàn)在比較少,以前多一些。我的焦慮原因是我到底有沒有創(chuàng)造力,或者我的創(chuàng)造力有沒有真正地表達(dá)出來,是不是足夠。這是我一直以來的。”
許知遠(yuǎn)將他現(xiàn)在的身份焦慮消解歸因于忙碌。“現(xiàn)在太忙了,忙得我已經(jīng)想不起來這事。可能我十年前會強(qiáng)烈,有很多對西方世界的焦慮。現(xiàn)在,遵從自己的經(jīng)驗(yàn),將自己已知的經(jīng)驗(yàn)和思考最大程度的展現(xiàn)出來。對我來說,是一種滿足。可能我就是一個(gè)二流作家,或者也是一流,不知道。但我盡量把我能有的一切、看到的、觀察到的、思考到的,展現(xiàn)出來、書寫出來、表達(dá)出來,對我來說,就夠了。”
許知遠(yuǎn)認(rèn)為,《青年變革者》這本書幫助他找到了某種召喚。“我有個(gè)更長的計(jì)劃是九卷本,它只寫了我要寫的1/9。我的人生,某種意義上被確定了也好,或者說它已經(jīng)有一段明確的方向。所以我也沒有太多搖擺的東西。它就像農(nóng)民干活一樣,下地、種地,每天種一點(diǎn)。我現(xiàn)在就這種心態(tài)。”
在許知遠(yuǎn)的構(gòu)想里,九卷本傳記里可能還包括李鴻章、林語堂。前者是晚清重臣,洋務(wù)運(yùn)動代表人物之一;后者是作家、翻譯家、語言學(xué)家,新道家代表人物。李鴻章出生于19世紀(jì)前葉,逝世于1901年;林語堂出生于馬關(guān)條約簽約之時(shí)、梁啟超領(lǐng)導(dǎo)的維新運(yùn)動序幕拉開的1895年,逝世于1976年。
他們倆主要生平居于梁啟超一前一后,與他一同構(gòu)成了19世紀(jì)到20世紀(jì)中國巨變的縮影。這是許知遠(yuǎn)的野心,也是他從2013年起,或?qū)⑿枰簧プ咄甑囊粭l自我召喚之路。“我都43歲了,也會更能跟自己的情緒共處了。這個(gè)漫長的計(jì)劃,它的重要性足夠超過我自己。我自己沒那么重要。”
“我自己沒那么重要”,這是許知遠(yuǎn)不經(jīng)意間重復(fù)了四五次的話。

青年梁啟超
有關(guān)“作家”這一身份,許知遠(yuǎn)說,他希望被認(rèn)為是一個(gè)比較有世界主義精神(Cosmopolitan Spirit)的中國作家。“我可以關(guān)心的不只是自己的經(jīng)驗(yàn)或本國的事務(wù),我可以關(guān)心更廣闊的事情。我第一本書就這個(gè)意思,對世界進(jìn)行廣泛的發(fā)言,十多年前就是這么寫,沒變過。”
自從2008年春讀到托尼·朱特的書籍,許知遠(yuǎn)就將他視作知識上的偶像。托尼·朱特身上那些非常清晰的判斷、典雅的寫作、廣闊的知識結(jié)構(gòu)、強(qiáng)烈的歷史意識,是許知遠(yuǎn)一直以來都特別渴望的。“他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知識分子精神,是一個(gè)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典范。”
許知遠(yuǎn)可能是當(dāng)代最堅(jiān)守“公共知識分子”身份的人。在他看來,過去十年,媒體妖魔化了知識分子,把他們變成了某種很偏狹的代名詞,或是激烈、邊緣。“不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中心。”
如今,他離他的知識偶像,離他一直所堅(jiān)守的公共知識分子更近了一步。但又似乎他并不一定會成為托尼·朱特。
比起梁啟超,許知遠(yuǎn)坦言,其實(shí)更好奇他所屬的那個(gè)年代。如果論與個(gè)體的呼應(yīng),他對郁達(dá)夫、魯迅這些作家的呼應(yīng)反而更強(qiáng)烈。“我一直想寫一本關(guān)于郁達(dá)夫的書,我想沿著他去南洋的路走一趟。他的情感世界觀,挺讓我有親切感。”
“可能有的時(shí)候意識不到,我是有現(xiàn)實(shí)能力的人。我不是純粹活在自己的書本世界的人,也不是那種為理念獻(xiàn)身的人,我沒那么勇敢,沒那么決絕。”勇敢是許知遠(yuǎn)描述托尼·朱特的一個(gè)關(guān)鍵詞。
許知遠(yuǎn)說,他身上有很多享樂主義的東西,過不了苦行僧的生活。他口中的享樂主義,其實(shí)是中國唐宋時(shí)期文人一直流傳下來的風(fēng)雅。他自嘲道,(這叫)流氓氣。
“一面郁達(dá)夫,一面托尼·朱特,我都有一些,都不太夠。”

43歲的許知遠(yuǎn),開始有了些變化——不管是與以一本《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年少成名的25歲相比,還是與三年前剛準(zhǔn)備面對鏡頭,成為一個(gè)談話節(jié)目的主持人,并意外地被卷入一場爭議討論而成為“網(wǎng)紅”相比。
他變得熟練。熟練面對鏡頭,熟練知道如何去采訪。但他也知道這不是個(gè)好現(xiàn)象,“變成套路都是很糟的事情。我挺怕變成太熟練,所以第四季要爭取要重新陌生化一點(diǎn)。主要是太忙碌了。忙碌會非常影響創(chuàng)作質(zhì)量。很多東西是閑散產(chǎn)生的,但沒有時(shí)間醞釀這些東西,每件事情都被排的密密麻麻。”
他說,他變得更容易理解別人,更有耐心了。
在接受采訪時(shí),他當(dāng)然希望每一個(gè)采訪者都能與他多聊聊《青年變革者》這本書,聊聊他費(fèi)心思地在書里創(chuàng)造空間感的出發(fā)點(diǎn),聊聊在戊戌變法之前的嘗試“強(qiáng)學(xué)會”為什么會失敗,其內(nèi)在的脆弱到底是什么…但他又理解,人生就是這樣。不是所有你想談的,別人就要跟你談。世界不是圍繞你自己運(yùn)轉(zhuǎn)的。
他開始不太愛喝酒,用跑步來幫助分泌多巴胺。他依然容易厭倦,但會盡可能收斂,不對周圍的同事、朋友造成壓力。
但43歲的許知遠(yuǎn),依然有不變的。
他嗜新。梁啟超傳第二卷未能排上他的日程,許知遠(yuǎn)找到了新的驚奇感——寫一本與日本有關(guān)的書。
他保持對意義的高需求。“事物都有其意義,我想找那個(gè)意義,或者賦予它意義。”即便是當(dāng)下,以“網(wǎng)紅”身份成為大眾文化眼中的一個(gè)符號,許知遠(yuǎn)也希望他這個(gè)符號蘊(yùn)含更多的意義、更多的維度,通向更多的可能性、更深入的東西。
他依然崇尚意外。面對外界誤以為《十三邀》里他和木村拓哉在尬聊,許知遠(yuǎn)稱,節(jié)目只是把我們倆的各種反應(yīng)——尤其是語言不通,翻譯的也不一定準(zhǔn)確——保留下來,這就是兩個(gè)陌生的不同語言之間交流的很正常反應(yīng)。“中國觀眾習(xí)慣了看表演性的談話。這對我來說,沒有意義。我希望它意外。”
甚至,他略有些憤慨于部分觀眾。“我問他,你像哪顆盆景?這很尬。這種尬不挺好的嘛,這是意外啊。他回答也挺好,他想成為一個(gè)根還不太穩(wěn)的。這多好的回答。這是真正的談話,意外、有趣的東西。”
不管變與不變,對43歲的許知遠(yuǎn)來說,更重要的是,作家歸來,他意識到“自己沒那么重要”。
以下是紅沙發(fā)專訪實(shí)錄:
作家許知遠(yuǎn)紅沙發(fā)專訪實(shí)錄
一、青年變革者

許知遠(yuǎn)在《青年變革者》新書分享會現(xiàn)場
紅板報(bào):在新書分享會,邀請不同地方的年輕人用方言朗誦《青年變革者》是誰的主意呢?
許知遠(yuǎn):是我的主意。也期望聽到他們對書的理解,這對我來說是有意思的。坦白說,書的活動不是為了我自己,甚至也不是為了出版社。本質(zhì)上真的希望梁啟超這個(gè)人,他的經(jīng)歷,他的故事能夠被年輕人、更多人去知道和理解。這個(gè)東西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是自己一個(gè)人的責(zé)任。梁啟超,他的遺產(chǎn)得到某種程度的復(fù)活,這是我應(yīng)該做的事情。
紅板報(bào):《青年變革者》這本書的靈感源泉和動力一直以來有發(fā)生過變化嗎?
許知遠(yuǎn):一個(gè)計(jì)劃或一本書,一旦開始,就會形成自身的動力。它不用老想著我的動力是什么,它接下來就會形成內(nèi)在邏輯,它的人物已經(jīng)開始建立起與其他人物的關(guān)系,你就不自覺尋找新的故事去推進(jìn)這件事情。
而且,當(dāng)你想寫了,完成它是必須要做的事情。不完成它的痛苦遠(yuǎn)遠(yuǎn)大于完成它的痛苦。完成它當(dāng)然很痛苦,但放棄它給你帶來的痛苦是更沮喪的。
紅板報(bào):第一卷完成是一個(gè)翻篇,寫《梁啟超傳》第二卷需要尋找新的動力嗎?
許知遠(yuǎn):不需要了。第一部已經(jīng)積累的大量的勢能動力。梁啟超流亡海外,康有為逃走了,他們的命運(yùn)會是什么樣子呢,它已經(jīng)積累了大量這樣的(勢能),你必須要追尋他們的命運(yùn),他們又會發(fā)生什么事情呢。
我需要更大量的資料收集,第二季是關(guān)系全球視角。梁啟超去了日本,去了很多別的國家。康有為也一樣,海外成立了保皇黨,跟孫中山有理念上的分歧、資金上的競爭、組織上的競爭。當(dāng)時(shí)全球英國、日本、美國、德國又是怎么看中國的。他們又跟這樣的流亡者的關(guān)系是什么?清政府,經(jīng)過維新變法后,巨大帝國系統(tǒng)內(nèi)部怎么逐漸走向瓦解?自身形成巨大的勢能,不需要我去推動它,只需要我去完成它。
紅板報(bào):《青年變革者》這本書聚焦在梁啟超這個(gè)人,還是他所處的時(shí)代?
許知遠(yuǎn):都關(guān)心。它們是互為一體的。如果你不能更清晰地描繪那個(gè)時(shí)代,那個(gè)人的特性也不會顯著。因?yàn)槿魏稳硕际翘幵跁r(shí)代之中,他不能脫離時(shí)代存在。但是一個(gè)時(shí)代如果沒有這些特別豐富和立體的個(gè)體,時(shí)代也變得很模糊。
我好奇那個(gè)時(shí)代。我對梁啟超個(gè)人的好奇也挺強(qiáng)烈,但沒有那么強(qiáng)烈。如果說我對個(gè)人呼應(yīng)更強(qiáng)烈,肯定還是郁達(dá)夫、魯迅這些人。梁啟超代表的是那個(gè)時(shí)代對我觸動特別大,所以我后來寫的是時(shí)代的精神。
紅板報(bào):寫梁啟超這個(gè)人,是因?yàn)樗緛硐衲艑懗蛇@樣,還是您把他寫得像您?
許知遠(yuǎn):是我把他寫得像我,不是因?yàn)樗裎摇K械膶懽鞫急厝粫绱耍际亲陨斫?jīng)驗(yàn)的投射。因?yàn)槟愀斫庾约旱慕?jīng)驗(yàn),會寫的更生動,別人會覺得像你。不是這樣的。
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沒有那種客觀的。因?yàn)槟阕约旱慕?jīng)驗(yàn),是最生動的、最清晰的,所以你在看別人經(jīng)驗(yàn)的時(shí)候,跟你相似的經(jīng)驗(yàn)?zāi)銜懙酶谩1厝粸榇恕?/p>
我不覺得這是錯(cuò)的。但只不過一個(gè)好的創(chuàng)作者,會意識到對方的寬闊,盡量也使我自己也這么寬闊,去理解你,否則就會很偏狹。
紅板報(bào):《青年變革者》是許知遠(yuǎn)的“作家歸來”,您希望大家怎么去認(rèn)識這種作家身份?
許知遠(yuǎn):我可能希望被認(rèn)為是一個(gè)比較有世界主義精神(Cosmopolitan Spirit)的中國作家。我可以關(guān)心的不只是自己的經(jīng)驗(yàn)或本國的事務(wù),我可以關(guān)心更廣闊的事情。我第一本書就這個(gè)意思,對世界進(jìn)行廣泛的發(fā)言,十多年前就是這么寫,沒變過。
紅板報(bào):寫《青年變革者》這本書,與一部分能對梁啟超這個(gè)人、這段歷史感興趣的讀者進(jìn)行溝通交流,這是您最期望的結(jié)果?
許知遠(yuǎn):我期望很多結(jié)果,這是其中之一。我其實(shí)也不太期望結(jié)果。寫作是自己的事情,副產(chǎn)品我真的不太想。我哪那么關(guān)心那么多后果。
二、十三邀

紅板報(bào):因?yàn)椤妒愤@個(gè)節(jié)目,賦予您一個(gè)身份,網(wǎng)紅。對作家身份的執(zhí)著,會與“網(wǎng)紅”有沖突或矛盾嗎?
許知遠(yuǎn):沒有,不太有。因?yàn)椤肚嗄曜兏镎摺肥且槐就?yán)肅的書,需要很多閱讀門檻。沒有之前大眾文化(賦予的)網(wǎng)紅身份,它不會有這么多關(guān)注。如果過去我做節(jié)目所帶來的關(guān)注度,能部分轉(zhuǎn)化到對梁啟超的關(guān)注,對我來說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要不然這樣一本書就是沉睡的。我覺得這很好,我也不要求所有人都從頭到尾讀完。有一點(diǎn)體會就好。如果你是廣東人,看到我對廣州的描述、對新會的描述,我相信你會感到很親切。你是個(gè)媒體人,你讀到我對時(shí)務(wù)報(bào)館的描述,也會感到親切。你找到一些能打動到你的片段就好了。我沒有要求所有人從頭到尾都讀完,沒有這樣的需求。
紅板報(bào):這種心態(tài)是一直都有嗎?很早以前是寫時(shí)評文章,其實(shí)是需要讀者的反饋。
許知遠(yuǎn):我從來都不強(qiáng)烈,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覺得寫完它比觀眾的反饋更重要。寫完它,基本對我來說就已經(jīng)完成了。后面的事情其實(shí)沒有那么關(guān)心。可能出于虛榮心,偶爾假裝關(guān)心一下,但其實(shí)心里不是真關(guān)心。
對我來說,寫作本身是最有樂趣的。寫時(shí)評也是這樣,寫完就完了,對它有什么直接的impact(影響),我沒那么關(guān)注,因?yàn)槲矣X得它是一個(gè)副產(chǎn)品。個(gè)人性格是這樣,我容易厭倦。就想去做別的事情。
紅板報(bào):過去幾年開書店、做播客、做《十三邀》、寫書,都是出于對陌生的好奇?
許知遠(yuǎn):對,我有嗜新癥。我老是期望被suprise,我需要驚奇感。可能心理比較幼稚吧(笑),小孩才需要驚奇感。
紅板報(bào):您曾提到您喜歡秩序,您覺得這和“嗜新”矛盾嗎?
許知遠(yuǎn):我覺得我一直喜歡矛盾的東西。它是很開放的,但又是有原則的;它是很混亂的,但它內(nèi)在又有秩序;它看起來高度感性的,但后面其實(shí)非常理性。我就喜歡這種很矛盾的東西,我也希望是這樣的。
其實(shí)我這本書也是這種感覺,有的人可能說它非常感性,有的人又說它史料特別多。兩者對我來說,是并存的。
紅板報(bào):您提到混亂但有秩序,但不是所有事情能一開始就看清它是混亂的秩序,只能一開始看到混亂的表象。您是怎么去判斷呢?
許知遠(yuǎn):跟自身經(jīng)驗(yàn)有關(guān)系。每個(gè)人內(nèi)在的秩序或者原則是長年的自我經(jīng)驗(yàn)形成的。所以要看你的性格,和你之前價(jià)值觀形成的過程。
比如我近幾年的事情,如果正常來看,肯定挺混亂的。書店賣這個(gè)又賣那個(gè),又開分店,做播客。十三邀是最典型的。你說這個(gè)節(jié)目,人物劃分看起來完全是混亂的關(guān)系,每個(gè)人都不相干,但它又有強(qiáng)烈的內(nèi)在秩序——都是我個(gè)人好奇心很強(qiáng)的延伸。我不覺得我找一個(gè)娛樂明星,去見一個(gè)歷史學(xué)家,一個(gè)詩人,一定不相干。他們有很多內(nèi)在相通的地方。我在乎他們怎么面對自我的轉(zhuǎn)折,他們怎么觀察自我和這個(gè)時(shí)代的關(guān)系,他們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都會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所以對我來說,這是內(nèi)在很有秩序的部分。而且他們幫我打開眼界,原來你是這么想問題的,這是我個(gè)人好奇心的延伸。
包括我寫梁啟超,看起來這么不相關(guān)的事情,但梁啟超書里出現(xiàn)強(qiáng)烈的空間感的變化,這跟我拍節(jié)目是很直接的關(guān)系。節(jié)目中也有很多空間,他只有在他的空間里才會發(fā)揮出他真正的作用。比如西川老師,我們?nèi)ふ夜潘聫R的時(shí)候,那種感覺才會凸顯出來,那跟我們在中央美院跟他聊天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梁啟超書里也一樣,我盡量把他放進(jìn)空間里來看待,所以這里面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對我來說又是相似的。
紅板報(bào):錄《十三邀》到現(xiàn)在,對您個(gè)人來說有變化嗎?
許知遠(yuǎn):可能也有變化吧。我覺得我做這個(gè)節(jié)目,還是產(chǎn)生某種改變。可能我更容易理解別人了,更有耐心了。可能第一季沒那么耐心。很大程度是,我對鏡頭不熟悉,鏡頭跟著你很煩。現(xiàn)在我就比較熟悉了。
紅板報(bào):您喜歡陌生,討厭重復(fù),那么對這節(jié)目您的激情還有嗎?
許知遠(yuǎn):我很熟練了。熟練就是個(gè)問題,變成套路都是很糟的事情。我挺怕變成太熟練。所以第四季要爭取要重新陌生化一點(diǎn)。
太忙碌了。忙碌會非常影響創(chuàng)作質(zhì)量。因?yàn)楹芏鄸|西是閑散產(chǎn)生的。沒有時(shí)間醞釀這些東西,每件事情都被排的密密麻麻,所以我要克服下我的忙碌。
紅板報(bào):您會刻意去尋找一段空閑時(shí)間嗎?
許知遠(yuǎn):我現(xiàn)在是一種交替式的休息。寫書就是我的休息。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梁啟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shí)候,就去管理公司。他們都說,管得很糟,也是一種休息。
紅板報(bào):和木村拓哉的“尬聊”又被爭議討論不斷?您覺得是尬聊嗎?
許知遠(yuǎn):他們誤以為吧,沒尬聊,挺好的。只是我們談話過程中,在同傳,有等待、反應(yīng)的時(shí)間。中國其他訪談節(jié)目把所有這些等待、反應(yīng)時(shí)間都剪掉了,這不是有病嗎?兩個(gè)人怎么可能這樣說話,你說話我立刻知道你要說什么,這不是談話。這不是瞎扯淡么。
我們只是把我們的各種反應(yīng)——尤其又是語言不通,翻譯的也不一定準(zhǔn)確——保留下來,這就是兩個(gè)陌生的不同語言之間交流的很正常反應(yīng)。
我們希望的是自然談話。中國觀眾習(xí)慣了看表演性的談話,而且很多設(shè)計(jì)好了,我要問這個(gè),然后你回答這個(gè)。這對我來說,沒有意義。我希望它意外。
木村談了很多有意思的東西。它很真實(shí)的呈現(xiàn)了木村。好多人覺得,我問他,你像哪顆盆景?這很尬。這種尬不挺好的嘛,這是意外啊。他回答也挺好,他成為一個(gè)根還不太穩(wěn)的。這多好的回答。這是真正的談話,意外,有趣的東西。
紅板報(bào):《十三邀》里,您有最喜歡的嘉賓嗎?
許知遠(yuǎn):給我?guī)砟吧母杏X就很好,當(dāng)然對方有思想,我就更開心了。到現(xiàn)場時(shí),我都想跟他們聊,我都好奇。
每個(gè)人的表達(dá)是不同的,大家最習(xí)慣的是語言表達(dá)。對方說的很精彩。但有的時(shí)候是無聲的表達(dá),他是通過別的表達(dá),甚至通過沉默來表達(dá)。
或者說語言說話不是他最主要的方式,那我們就不要苛求這種方式。可能有的人通過音樂就表達(dá)完了,舞臺上已經(jīng)表達(dá)清楚了,不需要你再用語言表達(dá)一次。你就接受這種表達(dá)的多樣化。
不要誤以為他只有跟你談成什么樣,才是最好的表達(dá)。不是這樣的。我覺得,破除我們腦子中對表達(dá)的那種非常單調(diào)的印象。表達(dá)很豐富的。我就覺得兩個(gè)人沉默不說,兩個(gè)人都挺好的。大家對“說話投機(jī)”這個(gè)事情,想得太單薄了。
紅板報(bào):那如果《十三邀》特別期采訪許知遠(yuǎn),您選擇怎樣的方式與自我表達(dá)?
許知遠(yuǎn):我沒那么多自我對話的熱情,我通過寫作來跟自我對話,不是語言。
紅板報(bào):希望《十三邀》未來做成什么樣?
許知遠(yuǎn):我喜歡兩個(gè)主播。去年6月份自殺的安東尼·波登,他有一檔節(jié)目《未知之旅》(Parts Unknown),通過食物出發(fā),去理解各地文化。他是那種自然真實(shí)。另一個(gè)是BBC的史蒂芬·弗萊(Stephen Fry)做了一期紀(jì)錄片,非常好看。很喜歡這兩個(gè)男人,他們身上充滿自由精神(Free spirit),同時(shí)又非常有探索欲,有張力。我也希望我的節(jié)目,很自由、有張力,也有很多意外。
三、作家與身份焦慮

紅板報(bào):十三邀里提到過“不合時(shí)宜的作家”,您覺得怎么不合時(shí)宜了?
許知遠(yuǎn):如果你一定說“不合時(shí)宜”是有自己的一套內(nèi)在價(jià)值觀,那我是。大學(xué)畢業(yè)出了第一本書,很年輕就是一個(gè)有名的媒體人,開了一家書店也很成功,如果你說我不合時(shí)宜,那可以說我是一個(gè)弄潮兒。
我每個(gè)階段都有自己的方式。我只不過內(nèi)在的價(jià)值觀比較強(qiáng),不追隨時(shí)代。我只是沒有世俗意義的寒暄,我喜歡真實(shí)的談話,不喜歡表面的談話。
紅板報(bào):您經(jīng)常問您的采訪對象,有身份上的焦慮嗎。那對您來說,有嗎?
許知遠(yuǎn):(沉默思考)有啊。現(xiàn)在比較少,以前多一些。我的焦慮原因是我到底有沒有創(chuàng)造力,或者我的創(chuàng)造力有沒有真正的表達(dá)出來,是不是足夠。這是我一直以來的。
現(xiàn)在好像沒那么強(qiáng)烈了,以前有吧,覺得應(yīng)該寫出一個(gè)重要的作品。我本質(zhì)上的焦慮是創(chuàng)造力的焦慮。其他的不太有。
現(xiàn)在太忙了,忙得我已經(jīng)想不起來這事。可能我十年前會強(qiáng)烈,有很多對西方的焦慮。當(dāng)時(shí)做媒體,做作家,做一個(gè)思想者,面對一個(gè)更成熟的西方系統(tǒng)時(shí),肯定會覺得自己很弱,很邊緣嘛。現(xiàn)在這種感覺也過去了,就覺得每個(gè)人珍視自己的經(jīng)驗(yàn)。你的經(jīng)驗(yàn),某種上是獨(dú)一無二的。那種杰出也好、不杰出也好,也沒有那么絕對主義的判斷。
遵從自己的經(jīng)驗(yàn),將自己已知的經(jīng)驗(yàn)和思考最大程度的展現(xiàn)出來。對我來說,是一種滿足。我現(xiàn)在,不想虛度光陰。可能我就是一個(gè)二流作家,或者可能也是一流,不知道,但我盡量把我能有的一切、看到的、思考到的、觀察到,能夠展現(xiàn)出來、書寫出來、表達(dá)出來,對我來說,就夠了。
包括我們公司也是,我們公司一個(gè)中小企業(yè),好像也沒有成長為一個(gè)大企業(yè)的欲望。我覺得我們把公司既有同事的創(chuàng)造力,盡量發(fā)揮到一個(gè)程度,它的結(jié)果也并不那么重要。
我好像處在這樣一個(gè)階段,不太有身份焦慮,很少,很淡。
紅板報(bào):忙碌到消解身份焦慮的原因是什么?
許知遠(yuǎn):因?yàn)檫@本書。我覺得這本書幫我找到了某種召喚。我只寫了1/3,我有個(gè)更長的計(jì)劃是九卷本,它只寫了我要寫的1/9。我的人生,某種意義上被確定了也好,或者說它已經(jīng)有一段明確的方向。所以我也沒有太多搖擺的東西。它就像農(nóng)民干活一樣,下地、種地,每天種一點(diǎn)。我現(xiàn)在就這種心態(tài)。
紅板報(bào):是有意識地創(chuàng)作這本書,做這些事情,來緩解焦慮,還是在慢慢過程中發(fā)現(xiàn)自己對身份的焦慮沒了?
許知遠(yuǎn):都有。跟年齡有關(guān)系,我都43歲了。你也會更能跟自己的情緒共處了。
我覺得這本書幫我找回了某種召喚。我要寫的這個(gè)九卷本的書,這個(gè)漫長的計(jì)劃,它的重要性足夠超過我自己。我自己沒那么重要,(當(dāng)然也很重要,因?yàn)槟惚仨毎阉鼘懲辏举|(zhì)上自己沒那么重要,那你老琢磨自己干嘛。
紅板報(bào):這個(gè)九卷本的工程,拋開宏觀的意義和目標(biāo),對您來說私人的情感是什么?
許知遠(yuǎn):自我的投射。這么復(fù)雜的世界,你所有的情感在那個(gè)歷史世界都會找到投射,都會找到印證。
紅板報(bào):投射之后,有找到自己疑問的答案嗎?
許知遠(yuǎn):還在找。如果答案找到了,后半生都虛無了。肯定在繼續(xù)找,這是一個(gè)一直的過程。
紅板報(bào):您會在意大眾了解您只是通過某一方面片面的印象嗎?
許知遠(yuǎn):如果你焦慮被誤解這種事情,那你就沒完沒了地?zé)馈V徊贿^有人被誤解更多,我可能就被誤解的多,但我也被理解的多。它必然有很多并存。
紅板報(bào):不管是十三邀、或者寫書,在被外界大眾誤解的同時(shí),尋求自己對自己的那份理解?
許知遠(yuǎn):寫作是跟自己共處。有的時(shí)候大家,包括媒體,會夸張這種誤解。因?yàn)橹徊贿^是因?yàn)檎`解或沖突容易傳播,但其實(shí)非常多的人是理解你的,但不愿意傳播正常的理解。
所以這事情跟我的關(guān)系不大,那是外部的事情。而且,在這樣一個(gè)反智的時(shí)代,我堅(jiān)定的聲稱自己是一個(gè)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沖突,這是一個(gè)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沒什么。
當(dāng)你進(jìn)入大眾傳播,就會帶來這樣的問題。你也有可能,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里,與大眾不發(fā)生關(guān)系,你的形象或狀態(tài)一直是那個(gè)樣子。這也可能是很多人選擇的路嘛。
但對我來說,未知的嘗試是有趣的。你不用擔(dān)心嘗試會招來各種誤解、問題,因?yàn)槿绻憧偸菗?dān)心這些,你就會失去生命力,就會僵化。而且,在任何正常的環(huán)境和語境中,一個(gè)人Controversial(富有爭議性),在西方世界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說明,你可以激起大家不同的感受。
我一畢業(yè),剛開始去報(bào)社工作,第一本書就挺Controversial(富有爭議性),在媒體世界。他們覺得你為什么會像外國人一樣寫這些新聞。這本書出來,好多人說像漢語家寫的。這都很奇怪的標(biāo)簽,所以我對這些沒有什么。
而且在這么糟糕的一個(gè)時(shí)代,所有人都知道這個(gè)時(shí)代挺浮躁、挺淺薄的,資訊非常扭曲,如果你被所有人喜歡,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且也沒有這樣的人。任何的大眾明星,都是被兩極化得一塌糊涂。
所以媒體應(yīng)該重建一些社會的基本常識。現(xiàn)在很多扭曲是缺乏常識構(gòu)成的。每個(gè)人都很焦灼,都急于表達(dá),很多情緒都是對日常生活的不滿,然后突然找到一個(gè)東西來發(fā)泄。
紅板報(bào):您提到這是一個(gè)反智的時(shí)代。作為一個(gè)作家,您會愿意回到哪個(gè)時(shí)代?
許知遠(yuǎn):郁達(dá)夫、魯迅,也可能討厭他們那個(gè)時(shí)代吧。每個(gè)人都會煩自己的時(shí)代,這很正常。誰會說喜歡自己的時(shí)代,有毛病。對另一個(gè)時(shí)代的渴望,是我們?nèi)祟愓5男睦恚鼘?shí)際是完成某種張力、某種心理需求。我想嘗試下80年代的中國是什么樣,包括五四之后的中國。都行。
紅板報(bào):回到80年代的中國,您還會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這條路?
許知遠(yuǎn):我不知道。我就好奇那個(gè)時(shí)代到底是什么樣子。我不是浪漫化。我就覺得,那還是一個(gè)整個(gè)社會很向上的階段。我想去一個(gè)富有朝氣的時(shí)代。我們現(xiàn)在是一個(gè)充滿怨念的時(shí)代。
紅板報(bào):您排斥商業(yè)世界嗎?
許知遠(yuǎn):我不。文藝復(fù)興都是美第奇家族支持的,美國菲茲杰拉德、海明威,迷惘的一代,當(dāng)時(shí)是廣告和商業(yè)最發(fā)達(dá)的時(shí)候,很多都是靠這些支持。他們寫的書是新的娛樂方式的一部分。
我從來沒有“啊,這是商業(yè)”,我們當(dāng)然生活在一個(gè)過度商業(yè)化的時(shí)代,這是因?yàn)槿宋牧α康娜酰皇巧虡I(yè)多么壞。所以我們讓它變得更強(qiáng)大一些。如果你看到我們賣的那些書,肯定覺得這個(gè)書店要死,肯定不能持續(xù)嘛。但我們已經(jīng)活了14年,活過大部分創(chuàng)業(yè)公司,我們活得也挺好的。
紅板報(bào):這是您身上獨(dú)有的特質(zhì)嗎?
許知遠(yuǎn):中國文人一直是這樣。只不過到了現(xiàn)在出了一點(diǎn)問題。過去十年,我們媒體妖魔化了知識分子,把他們變成了某種很偏狹的代名詞,或者是激烈、邊緣。不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中心。
我有現(xiàn)實(shí)能力。可能有的時(shí)候意識不到,我是有現(xiàn)實(shí)能力的人。我不是純粹靠理念為生的人,不是純粹活在自己書本世界的人。
紅板報(bào):做您的同事會很有壓力嗎?
許知遠(yuǎn):我是個(gè)對人很溫和的一個(gè)人。他們都跟我表示過,特別擔(dān)心自己很淺薄,很無聊。我特別容易厭倦,大家會很容易感到我的厭倦。我沒有那種刻奇,我朋友們應(yīng)該會感到我的厭倦。我對人很禮貌,但我想會有壓力。是吧?(詢問現(xiàn)場其他同事)
紅板報(bào):九年前,您曾寫過《庸眾的勝利》,到現(xiàn)在,韓寒已經(jīng)不再是青年文化現(xiàn)象和符號。似乎許知遠(yuǎn)成為了新的看似特立獨(dú)行的符號,您怎么看?
許知遠(yuǎn):這是無法避免的,都是符號。被符號化是所有事都不可避免的,要不然你無法認(rèn)知世界。麥當(dāng)勞是符號,魯迅、郁達(dá)夫、梁啟超也是符號,他們這些符號所蘊(yùn)含的意義和另一些符號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我一定要成為一個(gè)符號,我希望這個(gè)符號蘊(yùn)含更多的意義,更多的維度,通向更多的可能性,更深入的東西。
紅板報(bào):那是否可以理解庸眾是無可避免的?
許知遠(yuǎn):你不能把這個(gè)世界這么純粹化。任何時(shí)代社會主體都是盲從者居多。不是每個(gè)人都有獨(dú)立思想見解,只有一小群人。所以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有自己獨(dú)立的(思想見解),不是這樣的。他們要尋求自己的某種確認(rèn)、某種意義、價(jià)值、認(rèn)同,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有的符號會更長久,因?yàn)樗峁┑膬r(jià)值、意義、認(rèn)同更豐富,它可以更持久。有的符號當(dāng)時(shí)喧囂一時(shí),過段時(shí)間就被遺忘了,是因?yàn)樗N(yùn)含的內(nèi)在東西不夠多。
如果你對自己有要求,就盡量使自己成為一個(gè)蘊(yùn)含的信息、思想、情感含量更多的一個(gè)符號。而(追捧與否)這個(gè)東西跟每個(gè)符號沒關(guān)系,是別人的事情。我的責(zé)任是使我的寫作、我的觀察思考,我開的書店自身價(jià)值更豐富,這是我的使命,其他那些不是我的使命。
四、毛姆或薩特
紅板報(bào):您是一個(gè)不太愿意接受采訪的人嗎?
許知遠(yuǎn):對,我怕重復(fù)。
紅板報(bào):最近這段時(shí)間被問過最無聊的問題?
許知遠(yuǎn):“你為什么寫梁啟超?”
紅板報(bào):最有驚喜感的采訪問題?
許知遠(yuǎn):我忘了。他得懂一些這個(gè)書。為什么要致力于創(chuàng)造書里的空間感?對空間的描述這么重要?為什么強(qiáng)學(xué)會這么快就失敗了,內(nèi)在的脆弱到底是什么?得進(jìn)入書里的紋理,讓我意識到對方更懂這件事情,會有興趣來談。
紅板報(bào):托尼·朱特仍是您知識上的偶像?
許知遠(yuǎn):當(dāng)然是。我沒他那么勇敢。他有非常清晰的判斷、很典雅的寫作、廣闊的知識結(jié)構(gòu)、強(qiáng)烈的歷史意識,這些東西都是我特別渴望的。他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知識分子精神,是一個(gè)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典范。
紅板報(bào):對郁達(dá)夫有什么情感?
許知遠(yuǎn):我一直想寫一本關(guān)于郁達(dá)夫的書,我想沿著他去南洋的路走一趟。他的情感世界觀,挺讓我有親切感。
紅板報(bào):魯迅呢?
許知遠(yuǎn):有點(diǎn)害怕他。
紅板報(bào):為什么?
許知遠(yuǎn):太冷了吧。太sharp,太犀利了。我不是那種為理念獻(xiàn)身的人,我沒那么勇敢,沒那么決絕。
紅板報(bào):魯迅應(yīng)該不是傳統(tǒng)中文語境里的文人形象?
許知遠(yuǎn):對,他是有尼采精神的人。郁達(dá)夫挺像中國文人,我對他的世界挺好奇。(我身上)一面郁達(dá)夫,一面托尼·朱特,我都有一些,都不太夠。
紅板報(bào):毛姆或薩特,選擇成為哪一個(gè)?
許知遠(yuǎn):那肯定做毛姆。我身上有很多享樂主義的東西,我過不了苦行僧的生活。其實(shí)最想成為卡薩諾瓦,成不了,能力有限。他是真正具有游蕩精神的人。
數(shù)英用戶原創(chuàng),轉(zhuǎn)載請遵守規(guī)范
轉(zhuǎn)載請?jiān)谖恼麻_頭和結(jié)尾顯眼處標(biāo)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未經(jīng)授權(quán)嚴(yán)禁轉(zhuǎn)載,授權(quán)事宜請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quán)必究。
本文禁止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授權(quán)事宜請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quán),侵權(quán)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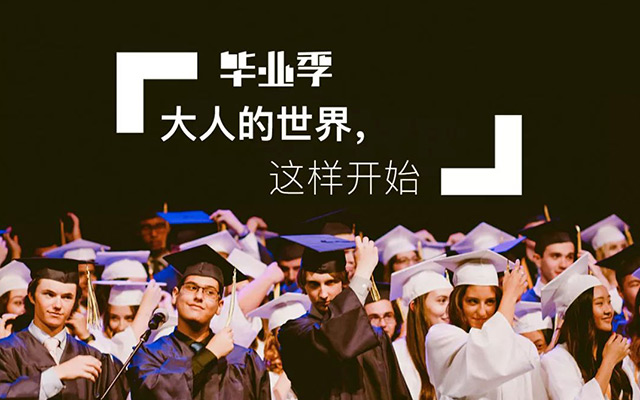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暫無評論哦,快來評論一下吧!
全部評論(0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