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lián)做的《新知》雜志休刊了,紙媒產品現(xiàn)在該如何活下去?
來源:好奇心日報
作者:劉璐天
原標題:三聯(lián)做的《新知》雜志休刊了,一個生不逢時的內容產品現(xiàn)在如何活下去?
配圖來自《新知》微博
與眾不同的雜志不僅開創(chuàng)了一個時代,而且創(chuàng)造了新社區(qū)。成功的雜志都可以視為“喚醒了一些頗有個性的人們,使他們認識到自己實際上屬于正在形成的某個新社區(qū)的成員”。
在創(chuàng)造新社區(qū)的過程當中,有些成功,有些失敗,有些受制于種種外力戛然而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甚成功的《新知》雜志中也能看出這種努力的過程。
近期,我們將推出有關雜志的系列報道。它們獨樹一幟,曾經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出任重要角色。
2013 年,三聯(lián)開始推廣一本新雜志。有人詢問當時的主編苗煒定位是什么,后者回答:“我們先編一本自己會看的雜志……如果這雜志能活下去,我希望它是各領域專業(yè)人士寫的,各領域專業(yè)人士看的,互聯(lián)網時代的博雅教育雜志。”
2017 年 4 月,這本名為《新知》的雜志暫停出版,恢復日期未知。

《新知》雜志,圖片來自@新知微博

《新知》暫緩出刊公告,圖片來自@新知微博
《新知》是雙月刊,2014 年正式發(fā)行。售價 20 元,19 開,每期 160 頁左右,文章幾乎全部由海外高校教授或文理科博士生撰寫,再加上一兩篇小說以及海外時髦知識分子的新作譯文。封面和內頁的插畫及配圖均出自國內知名插畫師和攝影師。雜志談論的都是些永恒的話題,如語言學、神話、建筑、人工智能,但用有趣的選題牽引出來:《英格力士》、《言必稱希臘》、《春暖開花造房子》、《腦機界面》。
休刊的消息于 4 月公布時,沒什么人討論它。《新知》官方微博上的公告只有百人轉發(fā)、60 人評論。2 個月后,有人在知乎提問“《新知》為什么停刊”,創(chuàng)刊人、原《三聯(lián)生活周刊》副主編苗煒出面澄清“只是休刊,還可能再出”,也同樣只引來百來條贊同和評論。
但對于它的忠實讀者們來說,這個消息來得太過突然。它在互聯(lián)網上有著穩(wěn)定的口碑,但并不盈利。它的盈利模式還是依賴廣告——但就算先把《新知》的小眾定位放在一邊,紙媒的廣告收入整體也在劇烈下降——此時做雜志,的確生不逢時。
好產品、壞市場,消費者習慣被智能手機和網絡完全改變——這些老生常談的話當然可以用來解釋《新知》的命運。但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問問題:一個小眾的內容產品,在如今紛繁復雜的情勢下如何找到生存機會?《新知》這樣的產品活下去,真的完全沒有可能嗎?
讀者并非不存在,只是被“隔絕”了
2015 年,《新知》每期固定讀者已經達到兩萬多名,這證明它并不缺乏受眾——2 萬人對于一本雜志而言的確無法維系其生存,但對于一本書而言是合格的成績。
如果我們回到上面的問題,你會發(fā)現(xiàn)它的主語是“一個產品”,而非“一本雜志”。同樣是內容的集合,《新知》作為書和作為雜志的命運會完全不同。
三聯(lián)的思路是辦雜志,這個決策意味著辦一本苗煒所說的“互聯(lián)網時代的博雅教育雜志”的時間被推遲了 7 年,因為三聯(lián)必須等待一個讓這本雜志合法的“刊號”。
在中國,刊號的管制比書號更為嚴格。書號由具備出版許可的國有出版社向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實名申請,按照出版社注冊的責編數量按比例發(fā)放。刊號的發(fā)放總量則更小,申請過程也更復雜。
苗煒給《新知》寫第一份策劃是在 2006 年,那不能算一個紙媒的壞時候,但 2013 年就完全不同了。雖然《新知》一年預算有 300 萬,但要覆蓋人工、稿費、印刷、發(fā)行等,尤其是北上廣機場渠道費用,高達 90 萬。
我們可以快速回憶一下 2013 年的事:全國期刊發(fā)行量同比下滑了 20%~30%,報刊亭開始大面積減少——2013 年,鄭州拆掉了最后一家報刊亭,而南京則有近一半報刊亭被拆除。與此同時,機場書店、商場超市書店等特殊渠道的“入網費”每一年還都在增長。
由于《新知》發(fā)行量較小,實體渠道的實銷率可能還趕不上網購,苗煒與京東、亞馬遜合作,同時與《三聯(lián)生活周刊》共用發(fā)行部分渠道,比如高校云集的北京海淀區(qū)。
因為鋪貨少,很多讀者傾向于通過訂閱購買《新知》,但他們又會面臨“在封面上能找到郵發(fā)代號、卻無法憑這個代號到郵局訂閱”的問題,因為“雜志起訂量達不到北京郵政管理局的要求,發(fā)行部認為沒有必要因此額外支付一筆費用”。編輯俞力莎干脆從第 17 期開始在目錄上印上了 27 個城市的經銷商聯(lián)系電話,方便讀者自己聯(lián)系。
換句話說,讀者并非拋棄了《新知》,而是無法獲得這些內容。

第一期《新知》雜志,圖片來自@新知微博
如果《新知》不是一本雜志
在苗煒寫出第一份策劃的 2006 年,人稱“老六”的張立憲推出了《讀庫》。后者同為雙月周期,317 頁,刊載 5000 — 50000 字的中篇文章,但拿的是書號,因此被稱作“雜志書(MOOK)”。
雜志和 MOOK 的本質區(qū)別在發(fā)行渠道和經營方式。簡單而言,前者所受的嚴格限制,后者則輕松得多,因為后者主要靠零售賺錢。
創(chuàng)立于 2011 年的《知日》同樣也是 MOOK,原本在磨鐵旗下的文治圖書部分出版了四期,隨后主編蘇靜獨立創(chuàng)業(yè),找到中信出版社合作。蘇靜團隊負責內容創(chuàng)作,而中信則負責出版發(fā)行。用中信出版社營銷編輯李曉彤的話來說,中信渠道分發(fā)的優(yōu)勢在于“地面店可以鋪得比較廣,新書也能爭取比較好的位置。”
在朝陽大悅城單向街書店的進門位置,顯眼地擺著《知日》第 32 期特輯《太宰治》,書店店員向我們介紹,這是最近《知日》賣得最好的一本。在最后一頁列出的零售名錄上,列著 80 多家網點;除了新華書店這樣的大眾書店,也包括單向街、西西弗、先鋒書店、Page 等獨立書店或精品連鎖書店,以及北京、杭州、福州、西安以及廈門的航站樓。
而《讀庫》甚至完全繞過了傳統(tǒng)的圖書渠道商。為了降低渠道成本、控制庫存,《讀庫》在 2008 年 2 月開出了淘寶店。在北京的鼓樓西劇場、雕刻時光咖啡廳,讀者還可以通過掃描二維碼下單。張立憲去年在接受《好奇心日報》采訪時表示,小眾書店和當當里《讀庫》的銷售份額已經無足輕重。

《知日》雜志,圖片來自@單向街圖書館

讀庫淘寶旗艦店
小眾定位,從來不是小眾產品消失的理由
《新知》是舍得做內容的,在市場推廣極其有限的情況下,這是它獲得讀者的唯一原因。
在 2014 年 1 月推出的試刊號《腦機界面》中,15 位特約撰稿人包括了浙江大學數學系教授蔡天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物理學博士萬維鋼、復旦大學英語系教師朱績松、特拉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博士候選人歐陽良祺等。
編輯俞力莎記得剛加入《新知》時,苗煒向她解釋為什么只讓專業(yè)人士撰稿,是“為了追求一種謙虛的寫作態(tài)度”。“不要以為采訪了幾個所謂的專家,看了幾本書,就真的能告訴讀者如何看待問題。這本雜志要讓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是真正具有發(fā)言權的人。”
由于采用約稿制,而非一般雜志的采編制,《新知》編輯團隊很精簡。只有美術總監(jiān)孫曉曦和圖片總監(jiān)田克是苗煒從外面請來的。插畫占到了每期雜志 30% 到 40% 的配圖。這部分是因為《新知》探討的主題都比較抽象。為了保證原創(chuàng)性,所有插畫師和攝影師都是孫曉曦和田克按照稿件內容特地找來的。在目錄頁,用來劃分欄目板塊的數字“1、2、3、4”每期都是由不同的插畫師手繪。



14、16、18 期目錄頁的不同設計




這一點,反而是《新知》與讀庫、知日等 MOOK 大致相同的特點——雖然它們在內容上的表現(xiàn)方式完全不同。
文章篇幅在 5000 — 50000 字的《讀庫》常收錄一些挑戰(zhàn)閱讀底線的文章,比如關于德國司法案例的系列文章和九十多頁的古羅馬建筑論文。而一些讀者還是會“逼著自己閱讀”,認為它們能夠“在高度專業(yè)化的基礎上,加上一點點小小的個人發(fā)揮”。
中信出版社一位的編輯在接受《好奇心日報》采訪時認為,《讀庫》已經做出了品牌,品牌穩(wěn)固就可以籠絡穩(wěn)定的讀者。雖然張立憲自己還對品牌的持續(xù)影響力存疑——2006 年訂閱《讀庫》的 1000 人里只有 400 人留到現(xiàn)在——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讀庫》已經順利存活了 11 年,有一萬三千多名訂閱用戶,從 2006 年的 0600 期做到了 2017 年的 1704 期。
什么才是小眾內容的合理生存方式?
《知日》主編蘇靜在 2011 年剛創(chuàng)立磨鐵的時候認為:傳統(tǒng)雜志依賴廣告的變現(xiàn)方式限制了其靈活性。他是在出版四期《知日》后才離開磨鐵的。隨后,他開始和中信出版社合作運營知日。
蘇靜前同事、磨鐵文治圖書部門原編輯徐杭記得,中信出版社為蘇靜提供了一個免費空間,讓他省去了房租,做書最主要的出版和發(fā)行成本也由中信承擔,因此蘇靜的主要開支是人員和營銷費用。
蘇靜把《知日》稱作一個“內容品牌”。在主要定位日本文化科普讀物的《知日》逐漸為人所知后,他開始開發(fā)知日官網、淘寶店知日 Store、日語培訓。在向媒體解釋為何要推出一系列和圖書無關的業(yè)務時,他把這些業(yè)務稱作“范圍經濟”。“我們要做的不是規(guī)模經濟,是范圍經濟,就像是我們打一個點作為基礎,然后往上面掛一些附加的內容。”
在《知日》之后,蘇靜還先后建立不同的團隊推出了《日和手帖》、《食帖》和《知中》,分別以生活方式、美食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主題,都是“基于垂直關鍵詞的內容” 。它們的定價在 39 至 60 元不等,其中《知日》賣得最好的一期銷售量高達 8 萬份。這些雜志書系列雖然不登載廣告,但如蘇靜自己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的那樣,“內容即廣告”。在翻閱《知日》第 24 期《雜貨》時,你會讀到一篇標題為《制皂情節(jié)》、帶有知日 Store 二維碼的文章;而封二、封三則分別是《食帖》、《日和手帖》的推廣文。
“關鍵就是雜志書培養(yǎng)起來的用戶群,一個有消費力的群體,擁有這個群體的關注度,你可以賺產品的錢,也可以賺媒體的錢。”蘇靜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垂直”這個詞也出現(xiàn)在張立憲的口中。起初,這是指在《讀庫》每年七本雜志之外再出版氣質相近的書籍,比如 2009 年的京劇書《青衣張火丁》、2011 年的《共和國教科書》、2012 年的生活美學類圖書《傳家》、2014 年的以色列女總理自傳《我的一生》。從 2015 年底起,他們還開始推出一些周邊,如豐子愷的畫冊、單幅畫片、筆記本和日歷本。
在當年接受《好奇心日報》采訪時,張立憲認為這更符合現(xiàn)代的商業(yè)邏輯——“不是在一本釣魚的書旁邊放一本種花的書,而是放一根釣魚竿”。

食帖在微博上的宣傳頁面
“以紙為特征的出版業(yè)和互聯(lián)網是對立的,這是我們認知帶來的最大誤解。” 5 月 14 日,蘇靜站在北京東城美術館后街的一間咖啡館里說。這是知中和做書主辦的一場演講,主題是“如何做一本好 MOOK”。蘇靜介紹知中的業(yè)務架構,是微博、微信和《知中》雜志。其中微博、微信是用來吸引用戶的免費內容,而《知中》則屬于付費內容。
從 2015 年 8 月起,讀庫的微信公眾號也開始發(fā)布制作精良的短視頻。它們的時長從幾分鐘到十幾分鐘不等,張立憲是這些視頻中的主角,介紹自己做的書。最火的一期在騰訊視頻上獲得了 78 萬次點擊,主題是林徽因——非常“讀庫”。
三聯(lián)的困境
我們曾詢問苗煒是否想過選用書號而非刊號來經營《新知》,他的回答是:“沒有,那就沒法做廣告了。”
這句話放在 2006 年的時候無可厚非,也許三聯(lián)只是把決定延續(xù)到了 2013 年。苗煒在回憶《新知》的遺憾時,感慨的依然是“它錯過了微信紅利期,沒有‘雜志出著,同時大力氣做微信號’。”
三聯(lián)并不是一個對市場變化姿態(tài)靈活的公司。和蘇靜一個人就能決定和中信成立“知日”這個品牌不同,三聯(lián)每做一個決策都需要考慮到一個龐大體制框架。兩件事會成為桎梏:緩慢的決策流程,以及有限的預算支持。
《新知》初成立時,文字編輯只有三個人,陳賽、陸晶靖和俞力莎,都是從《三聯(lián)生活周刊》冒著拿更低薪水的風險(從每月一結的“底薪+稿費”變成兩月一結的“底薪+編輯費”;當時在任的三聯(lián)主編朱偉和苗煒商議決定允許編輯們同時給周刊供稿,以補貼收入的下降),自愿加入《新知》的主筆或資深記者。哪怕后期《新知》的市場活動增加,也沒有聘請更多的營銷人手。
三聯(lián)書店的起源是 1932 年鄒韜奮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生活書店,1951 年三聯(lián)書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作為其副牌。在 2002 年,它被劃歸中國出版集團,2010 年改制為企業(yè),現(xiàn)為中國出版?zhèn)髅焦煞萦邢薰救Y子公司。
和很多傳統(tǒng)的媒體公司一樣,它被動地跟隨市場潮流,但都沒有想清楚這對自己意味著什么——2015 年,《新知》推出 Kindle 版,電子書賣 1.95 元,實體雜志賣 20 元,形成了尷尬的差距。
MOOK 的思路并非從未出現(xiàn)。2015 年底,苗煒離任,《三聯(lián)生活周刊》主筆王星成為《新知》主編,后者推出更專題化的主題,比如《偵探小說》、《新智人》。在俞力莎看來,王星的思路是把《新知》作為一場展覽的導覽手冊,通過線下活動立體化地呈現(xiàn)每期主題。
整個 2016 年,每出一期雜志,《新知》都會推出一到兩個沙龍活動,通過松果生活、三聯(lián)生活周刊和新知自己的微信、微博做宣傳。借助資源置換,《新知》在高校、中信書店獲得了一些小規(guī)模的場地。大部分活動是免費的,入場方式是購買一本《新知》雜志;個別收費在 300 元以上,則主要用于酒水供應。

中讀 App 頁面
但這樣的嘗試并不會迅速起效。它只是在原有框架下編輯思路的變化,而不是產品屬性的變化。
2016 年底,三聯(lián)書店出了兩個內部創(chuàng)業(yè)的新媒體項目——生活方式平臺“松果生活”和茶葉品牌“熊貓茶園”,開始尋求內容變現(xiàn)。它還成立了下級子公司“三聯(lián)生活傳媒有限公司”,將《愛樂》、《新知》和《三聯(lián)生活周刊》整合到該公司下。這家公司把希望寄托在一個名為“中讀 APP”的知識付費應用上,也把它作為 11 個主要募資產品之一,投資近 2 億元。
如果你使用過這個產品,你會發(fā)現(xiàn)它的用戶體驗并不友好。付費前需要購買虛擬貨幣,而購買的過程十分復雜。
這個應用將三聯(lián)書店旗下雜志的所有內容拆分開來,允許讀者花幾元單獨閱讀封面故事,或者支付 9.9 元訂閱喜歡的三聯(lián)專欄作者的文章;此外還設有“知識明星”主講的中讀音頻課程、以 UGC 為主導的“讀感”功能等。
去年 2 月,中國出版公布了 IPO 申報稿。按照《新知》編輯俞力莎的說法,中國出版集團上市后,《新知》有可能在中讀 App 這個項目的框架之下“促成復刊”。
這是一個友好的說法,而實際的情況可能是,因為“中讀”拆散了所有雜志的內容,作為一種獨立調性、希望作為“互聯(lián)網時代的博雅教育雜志”而存在的那個《新知》,永遠消失了。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載侵權必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授權事宜請至數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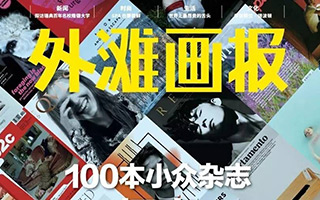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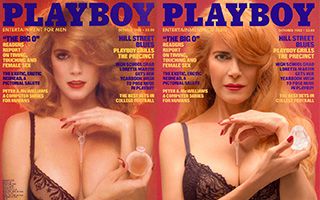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全部評論(1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