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管理、打擊謠言、說(shuō)服父母…疫情里的傳播學(xué)知識(shí)

雖然中國(guó)已經(jīng)不是非典時(shí)的中國(guó),我們有了更先進(jìn)的醫(yī)療技術(shù)、更高效的物流體系、更強(qiáng)大的政治地位,但當(dāng)我們?cè)僖淮蚊鎸?duì)疫情,某些地方機(jī)構(gòu)在大眾輿論面前,依然像個(gè)沒(méi)畢業(yè)的小學(xué)生。
我想討論一下,在這次疫情發(fā)生期間,上到政府下到每個(gè)市民,正在面對(duì)的幾個(gè)傳播學(xué)問(wèn)題:
我們都知道「堵不如疏」,為什么某些機(jī)構(gòu)還是企圖「控制」輿論?
我們都喊「不信謠不傳謠」,為什么一到疫情還是謠言四起?
很多人都說(shuō)“就差以死相逼了”,為什么就是「說(shuō)服」不了父母戴口罩?
非典在前,而新型肺炎的教訓(xùn)正在發(fā)生,如何讓人們「長(zhǎng)點(diǎn)記性」?
一、「控制」可以輿論嗎?
12月8日,武漢出現(xiàn)第一例新型肺炎患者;
1月2日,央視報(bào)道武漢《8名散布謠言者被查處》;
1月19日,武漢市疾病防御控制中心主任李剛稱:疫情可防可控;
1月21日,湖北省省委領(lǐng)導(dǎo)一同出席了春節(jié)團(tuán)拜會(huì)的文藝演出;
1月23日,湖北省長(zhǎng)王曉東接受采訪,稱武漢物資儲(chǔ)備和市場(chǎng)供應(yīng)是充足的;
1月24日,湖北省才尾隨各省,啟動(dòng)了1級(jí)響應(yīng)機(jī)制。
……
從武漢和湖北省的輿論操作方法可以看出來(lái),他們一直在試圖「控制」輿論。但無(wú)論是非典期間,還是當(dāng)下正在發(fā)生的新型肺炎,以及無(wú)數(shù)個(gè)輿論事件都告訴我們:輿論是無(wú)法控制的。
既然大家都知道「堵不如疏」的道理,為什么還是心存僥幸地想堵一下呢?
因?yàn)槎虏粚?duì),但是疏也是有bug的。
輿論是個(gè)放大器,它可以把好事和壞事,都千百倍地放大。在輿論監(jiān)督面前,疫情危險(xiǎn)可以被放大,恐慌情緒可以被放大,官員失職可以被放大!而沒(méi)有人喜歡放大自己的錯(cuò)誤……
于是,在失控的輿論面前,掩飾終于變成了失信,小錯(cuò)誤終于釀成了大敗局。
我們要清晰地認(rèn)識(shí)到一點(diǎn):我們要求官方機(jī)構(gòu)公開透明,時(shí)時(shí)接受輿論監(jiān)督是合法合理的,但在實(shí)際執(zhí)行中,這個(gè)方法是違背人性的、是極難落地的。
既然控制輿論不對(duì),不控制輿論又極難落地,官方機(jī)構(gòu)到底要怎么做?
這里我們要引入一個(gè)傳播學(xué)的理論 —— 議題設(shè)置理論(the agenda-settingtheory)。
伯納德·科恩對(duì)“議程設(shè)置”給過(guò)一個(gè)有影響力的表述,他說(shuō):“在多數(shù)時(shí)間,報(bào)界在告訴它的讀者該怎樣想時(shí),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訴讀者該想些什么時(shí),卻是驚人地成功” 。
這個(gè)理論告訴我們:通過(guò)設(shè)置社會(huì)議題,官方機(jī)構(gòu)雖然不能控制大眾說(shuō)什么,但是可以「引導(dǎo)」大眾討論什么。
做輿論傳播,就好比和大眾坐在一個(gè)大廳里開會(huì),如果你強(qiáng)硬地命令參會(huì)人員不準(zhǔn)玩手機(jī)、不準(zhǔn)小聲嘀咕、不準(zhǔn)走神,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通過(guò)設(shè)置會(huì)議議題,發(fā)動(dòng)參會(huì)人員一起討論一個(gè)又一個(gè)話題,從而間接地影響參與人員。
人都喜歡表達(dá)自我,而不是封閉自我。所以,議題設(shè)置理論是一個(gè)更符合人性的輿論管理方法。官方機(jī)構(gòu)要做的就是:既要對(duì)大眾公開事實(shí),同時(shí)要規(guī)劃大眾關(guān)注事實(shí)的議題。
以這次新型肺炎為例,湖北省的「輿論議題」可以是這樣的:
自我防御方法;
在家自檢肺炎方法;
相關(guān)機(jī)構(gòu)問(wèn)責(zé)以及糾察報(bào)道;
發(fā)熱門診定點(diǎn)醫(yī)院;
醫(yī)生救死扶傷事跡;
謠言舉報(bào)的途徑;
……
在重大疫情面前,把大眾可能會(huì)關(guān)注的每個(gè)議題設(shè)計(jì)好,有效地引導(dǎo)大眾,讓大家更多地去關(guān)注解決方法,而不是發(fā)生的問(wèn)題。這樣,才是既對(duì)公眾負(fù)責(zé),又政治正確的處理方案。
請(qǐng)記住:官方機(jī)構(gòu)要成為發(fā)起討論的人,而不能成為被討論的人。
二、面對(duì)疫情,如何減少「謠言」?
在疫情面前,不僅要防疫,還要防謠。既然要打擊謠言,我們就有必要深入研究一下謠言:
謠言是如何產(chǎn)生的?
為什么謠言往往比真相傳播力更強(qiáng)?
作為普通民眾,如何識(shí)別謠言?
打擊謠言的正確姿勢(shì)到底是什么?
1、謠言是如何產(chǎn)生的?
我們先來(lái)看一下新型肺炎期間流行的各類謠言,它們幾乎都可以被劃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關(guān)乎如何治愈新型肺炎的方法;
第二類是疫情到底發(fā)展到了什么程度。
這些謠言的特點(diǎn)我們可以用一個(gè)公式來(lái)理解:謠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這個(gè)公式是美國(guó)著名心理學(xué)家奧爾波特提出來(lái)的,這個(gè)公式牛就牛在,它非常簡(jiǎn)單地解釋了謠言誕生的兩個(gè)基本條件。一件事越是重大,大眾能獲得的信息越是模糊,謠言出現(xiàn)的幾率就越大。
謠言本身來(lái)自于我們對(duì)未知的恐懼,在恐懼中我們迫切地希望得到確切答案,但答案往往是不明朗的。正是人類的這種心理,給謠言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那么,為什么謠言往往比事實(shí)傳的更快更廣呢?
2、為什么謠言往往比真相傳播力更強(qiáng)?
你們看過(guò)《王牌對(duì)王牌》里的傳聲筒游戲嗎?每個(gè)隊(duì)友只能用動(dòng)作表達(dá)題板上的信息,并傳遞給身邊的隊(duì)友,最終由最后一名隊(duì)友猜測(cè)題板上到底寫了什么。

這個(gè)游戲之所以讓人啼笑皆非,就是因?yàn)樾畔⒃谵D(zhuǎn)述中被曲解的面目全非。很多謠言最初并不是謠言,是事實(shí)在人傳人的過(guò)程中,被曲解成了謠言。
同時(shí),這個(gè)游戲也完美地呈現(xiàn)了謠言傳播的三個(gè)機(jī)制:簡(jiǎn)化Leveling、強(qiáng)化Sharpening、同化Assimilation
傳聲筒游戲中,第二個(gè)接受信息的隊(duì)友,一定會(huì)遺忘部分信息,于是信息被“簡(jiǎn)化”了;
在轉(zhuǎn)述給下一個(gè)隊(duì)友時(shí),因?yàn)樗槐磉_(dá)了他記住的信息,并增加了自己新的理解,信息又被“強(qiáng)化”了;
于是,信息就在這種不斷簡(jiǎn)化、強(qiáng)化的過(guò)程中,看上去越來(lái)越「合理化」。
而人們之所以相信某條信息,不是因?yàn)檫@條信息是真相,而是這條信息讓他們更容易相信。
比如這兩條信息:吸煙抗病毒、養(yǎng)貓抗病毒。

坦白說(shuō),作為一個(gè)資深貓狗奴,雖然明知道第二個(gè)是謠言,我也更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而且隨著謠言越傳越廣,類似10萬(wàn)+的閱讀量會(huì)讓我們更容易相信它是事實(shí)。
真相往往是苦口的,而謠言常常是甜蜜的。
為什么謠言更有穿透力?因?yàn)橹{言在經(jīng)過(guò)了反復(fù)簡(jiǎn)化和強(qiáng)化之后,看上去更加可信了。又在信念同化的一群人中,得到了更多的轉(zhuǎn)發(fā)。
3、作為普通民眾,你如何識(shí)別謠言?
每次遇到重大事件、尤其是疫情時(shí),我們常看到「不信謠不傳謠」的呼吁,但有意思的是:我經(jīng)常看到傳這句話的人,自己不小心轉(zhuǎn)了某個(gè)謠言。
我們?nèi)绻氩恍胖{,第一步就是先學(xué)會(huì)識(shí)別哪些是謠言。我們常說(shuō)「謠言止于智者」,這句話其實(shí)是誤人子弟,謠言的傳播不可能靠智慧去中止。
因?yàn)槲覀冎爸v過(guò),謠言誕生最大的條件之一就是「事件的模糊性」。既然我們都不確定事實(shí)到底是什么,又如何判定這是謠言呢?
比如,有謠言說(shuō)鐘南山院士感染了肺炎,我們?nèi)绾慰恐腔廴ケ孀R(shí)真假?我們又沒(méi)有院士的電話和微信號(hào),只能等著院士自己辟謠。
「謠言止于智者」這句話我想改一下,叫「謠言止于傳播源」。
謠言本身是極難辨別真假的,所以我們不能通過(guò)內(nèi)容去判斷,但我們可以看傳遞信息的人的是誰(shuí),從而辨識(shí)信息的真假。
也就是說(shuō),重要的不是說(shuō)的話,而是誰(shuí)在說(shuō)話。
假如你正在看一篇有關(guān)疫情的公眾號(hào)文章,文章讀的你心情澎湃,在你想「轉(zhuǎn)發(fā)」之前,請(qǐng)?jiān)黾右粋€(gè)習(xí)慣,看看文章來(lái)源。
如果文章是原創(chuàng)的,那么就翻開作者過(guò)往的文章,看看他到底在寫什么;如果文章是轉(zhuǎn)載或引用的,那追查到文章最初發(fā)表的地方看看。
謠言有一個(gè)最大特點(diǎn),就是你找不到「?jìng)鞑ピ础埂?/strong>
例如,當(dāng)你看到「鐘南山院士也感染了肺炎」這條新聞時(shí),你是找不到它是被哪家媒體報(bào)道的。
再舉個(gè)例子,微信群流傳著一則「廣東省中醫(yī)院預(yù)防武漢肺炎方」的藥方:

隨后,廣東省中醫(yī)院在自己的微信里進(jìn)行辟謠。

有人會(huì)問(wèn),這張截圖里不是有傳播源嗎?就是廣東省中醫(yī)院啊?你這方法沒(méi)用啊?
這里要特別說(shuō)明的是:「?jìng)鞑ピ础共皇强从袥](méi)有標(biāo)注信息來(lái)源,而是要看這條信息是不是從傳播源頭發(fā)布的。
我們回看「廣東省中醫(yī)院預(yù)防武漢肺炎方」這條信息,如果這條信息是由廣東省中醫(yī)院的公眾號(hào)上發(fā)布的、或者是醫(yī)院某位醫(yī)生的采訪,那么我們才可以判定它不是謠言。
但有時(shí)候,我們還是低估了人性的丑惡,這條謠言就很難被判定。

傳謠的人將鐘南山院士的采訪進(jìn)行了PS處理,增加了一句「飲用高度酒對(duì)抗冠狀病毒」。
所以,對(duì)于截圖我們要格外小心,從識(shí)別謠言的難度而言:視頻>文字>圖片。
4、該如何減少謠言?
在疫情面前,謠言是比瘟疫更可怕的病毒。而打擊謠言,不能光靠「辟謠」。我們想一下,既然官方開始「辟謠」,那么證明謠言已經(jīng)流毒很久,辟謠只是馬后炮罷了。
該如何更有效地減少謠言呢?我認(rèn)為要從三點(diǎn)措施入手,分別是:增、減、便。
1)「增」,在重大事件面前,要做信息增量
這聽上去有點(diǎn)反常識(shí)。
很多機(jī)構(gòu)在面對(duì)輿論時(shí),常常擔(dān)心「言多必失」,怕對(duì)大眾造成恐慌。但這種“謹(jǐn)言慎行”的行為,反而給謠言生長(zhǎng)提供了溫床。
我們之前介紹過(guò)謠言誕生的公式:謠言=事件的重大性×事件的模糊性。
這個(gè)公式翻譯過(guò)來(lái)就是:在大事面前,人們?cè)绞堑貌坏酱鸢福驮綍?huì)胡亂猜測(cè)。
如果想讓用戶不造謠、不傳謠,最好的做法不是讓他們閉嘴,而是把更多的事實(shí)交給大伙嚼舌根。
所以,當(dāng)重大事件發(fā)生時(shí),機(jī)構(gòu)不僅要公開結(jié)果,更要時(shí)時(shí)公開進(jìn)度。用這種方式,不斷消除事件的模糊性,謠言自然就少了。
為什么大家會(huì)謠傳白巖松《新聞1+1》會(huì)采訪鐘南山院士?因?yàn)榇蟊姴⒉恢缹<医M如何看待目前的疫情,他們?cè)趦?nèi)心深處渴求鐘院士的發(fā)聲。
2)「減」,是指要減少信息的轉(zhuǎn)述
我們說(shuō)過(guò),很多謠言最初都是事實(shí),只是信息在轉(zhuǎn)述中被曲解了,所以變成了謠言。如果想減少謠言,我們就不能一味打擊那些被曲解的信息,而是要保證最初的事實(shí)不被曲解。
那么,政府/機(jī)構(gòu)要做的就是,盡量把一手信息直接送到受眾面前。
機(jī)構(gòu)可以先指定一批權(quán)威媒體,作為官方報(bào)道的渠道,例如CCTV、人民日?qǐng)?bào)、地方衛(wèi)視、騰訊新聞等。
建立自媒體矩陣,先于其他渠道發(fā)布一手的疫情信息、讓大眾養(yǎng)成上這些渠道獲取最新信息的習(xí)慣。
例如,湖北省就可以先開通湖北省的政府微博、公眾號(hào)、抖音藍(lán)V等媒體,作為疫情的官方發(fā)布渠道。
再針對(duì)湖北省的重點(diǎn)部門、重點(diǎn)單位、以及重點(diǎn)個(gè)人開通官方認(rèn)證的自媒體,例如湖北省衛(wèi)生廳、武漢市各級(jí)醫(yī)院、以及鐘南山院士的專家組。
聯(lián)合移動(dòng)、聯(lián)通等手機(jī)運(yùn)營(yíng)商,針對(duì)一個(gè)地域人群群發(fā)短信,讓信息直達(dá)所有民眾。
我們做火車進(jìn)入新的省區(qū)地界,都會(huì)收到“某某省歡迎你”的短信。新型肺炎這么大的疫情,更應(yīng)該好好調(diào)動(dòng)運(yùn)營(yíng)商的能量。
減少了信息的「中間商」,自然就減少了謠言的滋生。
3)「便」,指搭建便捷的舉報(bào)通道
一個(gè)國(guó)外的大學(xué)食堂,他們想讓學(xué)生養(yǎng)成健康飲食的習(xí)慣,例如少喝可樂(lè)、多喝礦泉水。他們起初在食堂大廳掛了很多廣告,并發(fā)給學(xué)生一些宣傳冊(cè),上面列的都是碳酸飲料對(duì)身體的危害。
但這種方式并沒(méi)有改善學(xué)生的飲食,學(xué)生們?nèi)匀毁?gòu)買高熱量的碳酸飲料。后來(lái)他們用了另一個(gè)方法,這種方法讓食堂里的礦泉水銷量大漲,而碳酸飲料的銷量降到了之前的30%。
這種方法非常簡(jiǎn)單:他們?cè)谑程玫馁?gòu)餐窗口擺滿了礦泉水,每個(gè)學(xué)生在購(gòu)買餐食時(shí),都可以隨手拿走一瓶。
很多宣傳之所以無(wú)效,不是民眾不認(rèn)同宣傳內(nèi)容,而是參與方式太復(fù)雜。
舉報(bào)謠言、舉報(bào)不作為、或者是募集捐款都是一個(gè)道理,政府/機(jī)構(gòu)不僅要做宣傳,更要搭建一條便捷的通道,讓人們可以分分鐘參與、不費(fèi)力地行動(dòng)。
這次新型肺炎時(shí)期,我們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就在中國(guó)政府網(wǎng)的公眾號(hào)上開啟了互聯(lián)網(wǎng)+舉報(bào)熱線,大家可以點(diǎn)擊小程序,舉報(bào)防控不力、緩報(bào)瞞報(bào)等行為。這個(gè)措施值得我們給一個(gè)大大的贊!

三、如何「說(shuō)服」父母戴口罩?
在疫情出現(xiàn)早期,和全國(guó)疫情報(bào)道共同出現(xiàn)在熱搜里的話題竟然是:如何「說(shuō)服」父母戴口罩?

為什么每天都注重養(yǎng)生的父母居然不惜命啦?為什么父母寧愿相信「小龍蝦是某某陰謀」、「包了保鮮膜的西瓜細(xì)菌更多」這些謠言,也不愿意相信身邊正在發(fā)生的危險(xiǎn)?
下面我就借助營(yíng)銷學(xué)理論來(lái)拆解一下,說(shuō)服父母的正確方法。
我估計(jì),大部分網(wǎng)友是這樣勸父母戴口罩的:
先轉(zhuǎn)發(fā)了幾篇疫情蔓延的公眾號(hào)文章給父母,叮囑了好幾句要戴口罩,然后父母輕飄飄地回了句“沒(méi)事兒”;
見父母沒(méi)說(shuō)通,你又追加了幾篇相關(guān)文章說(shuō)明疫情真的很嚴(yán)重。可父母的意思是“我們看著辦兒”;
于是你急了,說(shuō)了幾句“逼宮”的話,然后父母也急了,你們開始進(jìn)入日常爭(zhēng)吵模式……
這種方法為什么會(huì)失敗?因?yàn)槟阍谂Α刚f(shuō)服」父母,而不是在「說(shuō)動(dòng)」父母。
「說(shuō)服」是辯論技巧,它的核心方法是 “擺事實(shí)、講道理”,辯手通過(guò)自己的語(yǔ)言技巧,說(shuō)到對(duì)方啞口無(wú)言、無(wú)力反駁。某種意義上,說(shuō)服和打服、降服是一樣的,往往代表你贏、對(duì)方輸。
而「說(shuō)動(dòng)」是談判技巧。什么是談判?談判就是雙方為了共同利益的協(xié)商行為。注意「協(xié)商」這個(gè)詞,這個(gè)詞背后的意思是讓步、妥協(xié)、小心呵護(hù)雙方的關(guān)系。
大多數(shù)人,在勸說(shuō)父母戴口罩這件事上,犯下的最大錯(cuò)誤就是:你不小心用了一種強(qiáng)者對(duì)弱者說(shuō)話的姿態(tài)去灌輸一個(gè)觀點(diǎn),但在家庭地位中,父母才是“老大”,我們只是“小弟”。
一旦我們?cè)噲D去「說(shuō)服」父母,我們很容易把談話變成一場(chǎng)辯論、變成一場(chǎng)勝負(fù)之爭(zhēng)。那么父母反駁的就不再是該不該戴口罩這件事,而是自己的臉面。
事實(shí)上,當(dāng)我們想要讓對(duì)方認(rèn)同一種觀點(diǎn)時(shí),不能把焦點(diǎn)放在觀點(diǎn)本身上,要放在讓對(duì)方認(rèn)同的心理邏輯上。
2018年,瑞典隆德大學(xué)的幾位學(xué)者,做過(guò)一個(gè)試驗(yàn)。他們找來(lái)了一批人,這批人要答一份涉及12道政治觀念的判斷題。
比如,政府應(yīng)該給小學(xué)生提供免費(fèi)的作業(yè)輔導(dǎo)嗎?受試者要在完全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狀態(tài)線上選定一個(gè)點(diǎn),例如,他可以選擇50%的同意。
答完了這12道題,研究人員把受試者請(qǐng)到了另一個(gè)房間,讓他們解釋一下他們選擇這個(gè)選項(xiàng)的原因。但是研究人員卻私下調(diào)換了答案。例如本來(lái)張三選擇了90%同意,研究人員改成了10%同意。
但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人都沒(méi)發(fā)現(xiàn)自己的答案被篡改了。不僅如此,他們還振振有詞地,對(duì)被篡改后的假答案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一周之后,研究人員又把這批人找來(lái),并且告訴他們答案被篡改過(guò)了,但是受試者們堅(jiān)持那就是自己最初的選擇!而且越是那些被他們解釋過(guò)的答案,他們就越發(fā)堅(jiān)定自己的立場(chǎng)。
這個(gè)實(shí)驗(yàn)可以得到兩個(gè)結(jié)論:
1)人們往往記不住自己的選擇。心理學(xué)上,稱這種效應(yīng)叫“選擇失明”;
2)在心理上,人們?cè)诤醯牟皇鞘聦?shí)對(duì)錯(cuò),而是自己能否言行一致。
這個(gè)時(shí)候,你就應(yīng)該明白了,當(dāng)你問(wèn)出“疫情這么嚴(yán)重,為什么你還不肯戴口罩?”時(shí),你的說(shuō)服工作就已經(jīng)徹底失敗了。
本來(lái)父母可能還沒(méi)決定戴不戴口罩,可一旦你逼他們說(shuō)了自己不愿意戴口罩的原因,為了保持心理上的言行一致,他們就堅(jiān)定了不戴口罩是對(duì)的。
這個(gè)心理機(jī)制是引發(fā)我們勸說(shuō)失敗的關(guān)鍵原因,但如果利用恰當(dāng),也可以成為我們說(shuō)動(dòng)他們戴口罩的關(guān)鍵方法!
要拋棄「擺事實(shí)、講道理」這種做法,不要試圖向他們「灌輸觀念」,而是要「植入預(yù)設(shè)觀念」。
我們講過(guò),人的選擇往往沒(méi)有那么理性。所以,我們要在父母的大腦里植入「你本來(lái)就是會(huì)戴口罩的人」,而不是「你現(xiàn)在應(yīng)該去戴口罩」。
比如,當(dāng)你爸說(shuō)這里沒(méi)事,不用戴口罩。你就可以嘗試這樣去回答:
“爸,這不像你啊!你一直都是特別注重養(yǎng)生的人啊!在咱家那邊您也是高干子弟,你肯定會(huì)第一個(gè)響應(yīng)國(guó)家號(hào)召,帶領(lǐng)咱家親戚一起戴上口罩!”
還有一點(diǎn)要注意:人在突然接受一個(gè)新觀念時(shí),都是猶豫的,內(nèi)心其實(shí)是沒(méi)有選項(xiàng)的,一般都需要一段時(shí)間的消化,才能接納新觀念。但是我們常常發(fā)過(guò)去幾篇疫情信息之后,就讓父母立刻馬上去“執(zhí)行”,這其實(shí)是反人性的。
你要知道,讓你媽戴口罩去買菜,和讓你媽穿熱褲去逛街可能是一回事。請(qǐng)子女們記住:當(dāng)所有技巧都失敗后,對(duì)父母的耐心就是我們最大的技巧。
四、如何讓人們「記住」這次教訓(xùn)?
兩次重大疫情,都是人類的口舌欲引起的。所以,有網(wǎng)友戲稱:這次疫情應(yīng)該叫“野味肺炎”。我認(rèn)為這個(gè)稱號(hào)的價(jià)值簡(jiǎn)直可以作為兩會(huì)提案,它完全符合傳播學(xué)的邏輯。
想要人們記住一次重大事件,很多時(shí)候都是列舉事件造成的損失和苦難。但是我們想一想,當(dāng)我們高考結(jié)束后,有多少人能還記得南京大屠殺在哪一天?死了多少名同胞?大部分人真正記住的是「南京大屠殺」這五個(gè)字,以及這五個(gè)字帶我們的感受。
如果當(dāng)年歷史課本把「南京大屠殺」稱作「南京事件」,這件事的流傳度會(huì)減弱太多,給后人帶來(lái)的那種屈辱感也會(huì)降低很多。
對(duì)于一個(gè)歷史事件而言,命名大于一切。
比如「918事變」。聽到這個(gè)名字,很多學(xué)生可能還要在記憶里查找「918事變」是哪一件事?偶爾還會(huì)把「七七事變」和「九一八事變」搞混。但是這名學(xué)生永遠(yuǎn)不會(huì)搞混「太平天國(guó)運(yùn)動(dòng)」和「義和團(tuán)運(yùn)動(dòng)」。
我們常常責(zé)怪國(guó)人沒(méi)記性,但在一個(gè)信息爆炸時(shí)代,我們永遠(yuǎn)不要高估人們的心智容量。
如果我們想讓后代人記住這次新型肺炎的教訓(xùn),就要把所有信息濃縮在一個(gè)簡(jiǎn)單的名字里,而不是一個(gè)幾百字的歷史記錄里。
那么,「非典型肺炎」、「SARS」也很簡(jiǎn)單、也讓我們記住了。與它們相比,那么「野味肺炎」這個(gè)名字好在哪里?
首先,「非典型肺炎」和「SARS」只是醫(yī)學(xué)名稱,這種名字只能起到科普作用,而一個(gè)疫情事件,我們最該讓后代人記住的是如何防范疫情。「野味肺炎」直接點(diǎn)明了引發(fā)疫情的原因是吃野味,這才是最該被記住的因素。
我們不是要人們記住疫情,而是要人們記住疫情的成因。
在未來(lái)的日常生活中,我們不會(huì)經(jīng)常提及「新型肺炎」這么嚴(yán)肅的詞,但是我們可能常常會(huì)談到「野味」這個(gè)詞。
尤其是當(dāng)你走到一家賣野味的飯店,在幾個(gè)當(dāng)?shù)嘏笥训膽Z恿下,本想點(diǎn)一只野味嘗嘗鮮。此時(shí),你也許會(huì)突然想起有個(gè)恐怖的傳染病叫「野味肺炎」……
所以,「野味肺炎」可以把低頻詞「肺炎」,和高頻詞「野味」捆綁在一起,這樣不僅便于記憶,更容易喚醒記憶。
便于記憶、便于記住疫情成因、容易喚醒記憶,這是「野味肺炎」這個(gè)詞的好處。
具體在事件的宣傳上,我們還可以做兩件事:
第一,可以給這個(gè)「野味肺炎」設(shè)計(jì)一個(gè)logo,比如這樣:

人類的大腦記憶是視覺的。我們即便讀到文字,也要“翻譯”成畫面才能被大腦理解。一個(gè)好的LOGO可以便于我們對(duì)事件有更直觀地了解。
第二,針對(duì)「野味肺炎」事件,可以鼓勵(lì)創(chuàng)作一些大眾文藝作品,比如電影。
針對(duì)南京大屠殺,我們就有《南京南京》這樣的電影;針對(duì)唐山大地震,我們也有同名電影《唐山大地震》。而「野味肺炎」這部電影,已經(jīng)具備了一部?jī)?yōu)秀電影的關(guān)鍵因素:
主角,鐘南山院士;
反派,瞞報(bào)、緩報(bào)疫情的官員;
英雄,湖北醫(yī)院廣大醫(yī)護(hù)人員們;
沖突,各級(jí)醫(yī)院反抗官方不作為,聯(lián)合向社會(huì)求助;
細(xì)節(jié),女護(hù)士為了方便穿防護(hù)服,剪掉滿頭秀發(fā)。
我們來(lái)總結(jié)一下:
1、可以「控制」輿論嗎?
官方不能控制大眾說(shuō)什么,但是可以利用「議題設(shè)置理論」,引導(dǎo)大眾討論什么。
2、面對(duì)疫情,如何減少「謠言」?
對(duì)機(jī)構(gòu)而言,可以做信息增量來(lái)消除事件的模糊性;要減少信息的轉(zhuǎn)述;搭建便捷的舉報(bào)通道;
對(duì)于個(gè)人而言,可以通過(guò)尋找「?jìng)鞑ピ础谷プR(shí)別謠言。
3、如何「說(shuō)服」父母戴口罩?
「說(shuō)服」是個(gè)錯(cuò)誤的觀念。不要試圖向他們「擺事實(shí)講道理」,而是要「植入預(yù)設(shè)觀念」。
4、如何讓人們「記住」這次教訓(xùn)?
事件的命名大于一切。
比病毒更可怕的是人心,比疫情更危險(xiǎn)的是輿情。在疫情面前,我們打的不止是病毒戰(zhàn),還是一場(chǎng)信息戰(zhàn)。一起加油!
數(shù)英用戶原創(chuàng),轉(zhuǎn)載請(qǐng)遵守規(guī)范
轉(zhuǎn)載請(qǐng)?jiān)谖恼麻_頭和結(jié)尾顯眼處標(biāo)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未經(jīng)授權(quán)嚴(yán)禁轉(zhuǎn)載,授權(quán)事宜請(qǐng)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quán)必究。
本文禁止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授權(quán)事宜請(qǐng)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hào)(ID: digitaling) 后臺(tái)授權(quán),侵權(quán)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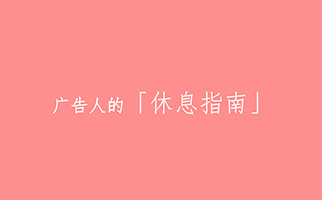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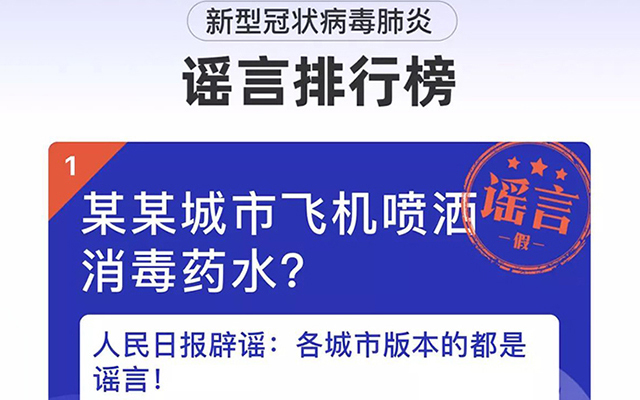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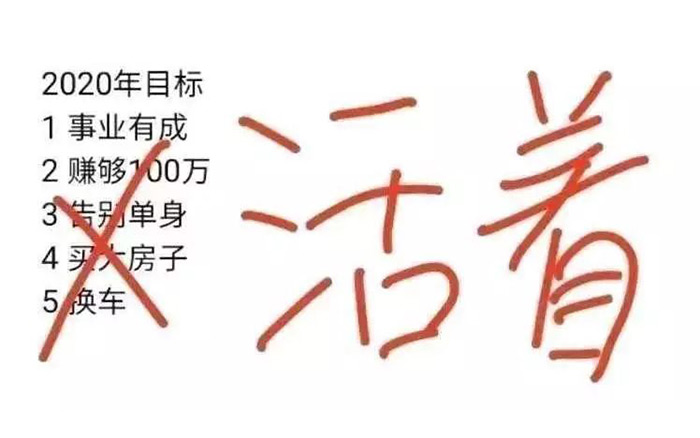



評(píng)論
評(píng)論
推薦評(píng)論
全部評(píng)論(3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