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故事:大猩猩可以騎在山羊背上嗎

前些日子,在臺北美術館看了關于楊德昌的首個完整回顧展《一一重構:楊德昌》。
楊德昌不是電影專業出身,他求學時是在美國學軟件的,做過軟件工程,直到34歲某天他看了沃納·赫爾佐格的《天譴》,頓悟了他需要拍電影。
啟發了楊德昌的沃納·赫爾佐格,也拍過很多特別有意思的紀錄片。《在世界盡頭相遇》是講南極的奇遇,里頭有一只瘋企鵝,與同伴們背道而馳,不去海邊或棲息地,固執地奔向內陸的群山。如果是人類,這企鵝注定也是某種天才。影片開頭他還提出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為什么像黑猩猩這樣的高級動物不去利用低級生物,它完全可以騎著一頭山羊在夕陽里揚長而去。”
我和初中同學、朋友WW談論這個問題,他和我說到之前看法國紀錄片《海洋》,里面有海豹會躺在水面上,用石頭敲開肚皮上的堅果吃。
恰好赫爾佐格也拍了南極的海豹,它們在水底發出的召喚聲——并非一般動物的叫聲,簡直是電子樂效果器,南極的科學家覺得這像是Pink Floyd。
進而WW提出“為什么人要拿動物作為自己的精神象征?為什么動物擬人化的時候人最覺得可愛?”我認為人類就是喜歡奴役別人,擬人化就是奴役它們,猩猩可沒有想奴役山羊,豹子獅子對山羊也是生死關系,人總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熱衷于權力。
WW說:“沒錯,歸根結底是取消對方的獨立價值。”
WW是那種不在乎別人怎么看他的人,本科讀的是化學專業材料學,畢業后去廣州的工廠做了近一年保安,因此有時間讀東方哲學。考了人大的相關專業研究生,得機會去法國交換一年,回來又讀博,繼續研究古代文獻歷史。
我總覺得他是像楊德昌頓悟,逆著走向群山的企鵝那樣,屬于非做這件事情不可、骨子里的。

對此他認為“談不上喜歡,我也不知道我喜歡什么,理工科有意思的是發現與發明,人文我覺得很多都挺沒意思的,目前覺得只有創作這個事情本身是值得探究的。”
我們的工作特別需要每個人都在乎別人怎么看他,他得對某些事情有強烈的喜歡。這樣他才能被社會規范進來,參與到MBTI分類、小紅書tags、趨勢生活方式的種種圈里來,才能有跡可循。
萬一TA都像楊德昌那樣看個電影就頓悟了,那方案就不好寫了,Slogan得熄火了。
創意文化產業正進入轟轟烈烈的自我營銷和自我奴役的階段,大眾審美情趣徘徊在滑稽與趣味之間,多元個性是吹泡泡,WW這種人的獨立價值太強,廣告業的TA里其實容不下他。
確實他也是不消費的那種人,非常簡樸地活在充盈的精神世界。我喜歡和這樣的人聊天交流,而工作里卻需要相反的情形,這是虛偽矛盾。
不管在不在乎別人怎么看自己,創作可能確實是我們的一線生機。
記錄每一個在場故事
2023數英獎,以“在場”為主題,匯聚了百個行業人物的在場故事,真實鮮活,耐人尋味,歡迎前往活動專題頁查看更多故事。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范轉載侵權必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授權事宜請至數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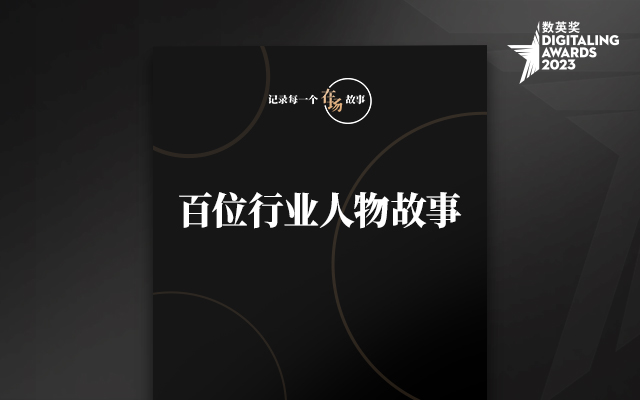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暫無評論哦,快來評論一下吧!
全部評論(0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