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故事:我已經不掙扎了

我從實習開始就不愿意干廣告,因為覺得弱智。這個感覺到今天還在。唯一認真的職業理想就是進媒體干新聞。
上學的時候,每周都會買《經濟觀察報》,那時候《經觀》剛創刊沒幾年,有一股很沖的天真氣息,完全不是現在這種浪費紙的樣子。對我來說,那就是外面的世界為我搖下來的車窗。

當時許知遠還在里面當主筆,團隊里還有很多不錯的媒體人。最年輕的一位編輯叫符郁,我覺得我是她的粉絲,可能是因為她也很年輕,代表了我能夠得著的夢想,也代表了我未來想要的工作和生活。
2005年的元旦,符郁在北京因為煤氣中毒去世。我很震驚,從符郁去世后,好像再有哪個文化偶像去世我都沒有什么真正的反應了。對死亡再也不會使用敬語,死了就是死了,不是走了。
來北京之后,對媒體的幻覺還在,感覺廣告只是臨時掙口飯吃,每天都惦記著要回報社上班。
有一天看到北京青年報在進行社會招聘,就報了名。筆試3個多小時,通過之后下一輪是去地壇書市實地采訪,寫一個稿在下午3點之前發到指定郵箱。
地壇書市除了書攤子就是賣烤腸的,還有很多肚子,肚子上都掛一個黑色腰包,沒什么可以采的,喝了一瓶冰紅茶就走了。
到家改完稿子之后感覺實在是太垃圾了。于是開始能理解,為什么紙餡包子這種新聞能出來。那會整個人非常沮喪,稿子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發。之后發現因為網速原因發送時間晚了幾分鐘。
結果必然是沒有進入第三輪面試。
當時寫的什么東西早就忘了,就對地攤上的遮陽布印象很深,為什么這么稀疏還能防曬,到底是什么材質。
后來知道整個招聘報名人數有幾千人,其中還有很多是牛津和哈佛的畢業生,內部調崗的人也要一起考試競爭。但總共只招十個人。無論從哪個角度考慮,都不可能輪到我。
不過后來反思了一下,到了地壇書市不知道該寫什么,就像現在做內容選題不知道該做什么一樣。肉眼看到水面之上無事發生便覺得真的無事發生,說明對新聞行業只是空有熱情,沒什么真實的能力。考不上主要還是自己的問題,干不了媒體也正常,可能我根本就不是那塊料,對媒體行業只是有一種生活方式層面的向往,對社會也沒什么真正的關心,那種熱情的本質,和三十年代德國社會把政治生活審美化一樣。
在廣告行業瞎混十幾年后,我已經不掙扎了,之前在環時上班的時候,北青大樓就在旁邊,來來去去早就毫無波瀾了。看這幾年的情況,反而會因為當年進不去媒體而偷笑。而且比干廣告更差勁的工作太多了。廣告行業因為沒用,反而也沒危害,還能掙點小錢,贏得一些點贊什么的。我這樣勸自己。
但是一到冬天,元旦假期左右,我還是會想起符郁,和二十年前想去的北京。符郁的博客文章當年都打印了,現在還留著,但是不會再看了。
那一代在北京的媒體人給我留下了一些幻覺,等我長大之后趕過來,他們已經散場了,整個北京都熄燈了。
現在有時候路過國貿橋,覺得這個地方已經很陳舊,開始長草。我覺得加班的日子總有一天會結束的,我的勞碌總有一天會停下來,不看書,不說話,不買東西,什么也不關心,每天去國貿停車場里面放羊,早晚各去一次,保安管不了我的。
記錄每一個在場故事
2023數英獎,以“在場”為主題,匯聚了百個行業人物的在場故事,真實鮮活,耐人尋味,歡迎前往活動專題頁查看更多故事。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范轉載侵權必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授權事宜請至數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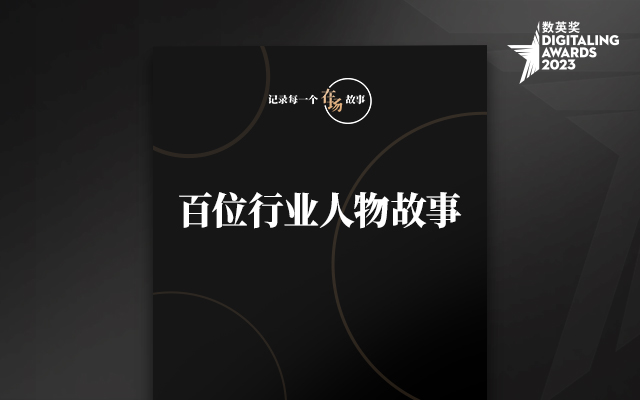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全部評論(2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