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革了命”的維基百科,與進化中的知識協(xi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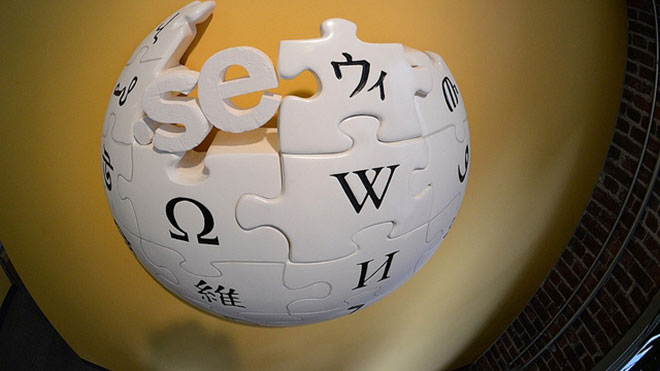
再發(fā)深度長文,是因為從互聯(lián)網(wǎng)早期民主機制下“人人皆可編輯”的網(wǎng)絡文化已經(jīng)逐漸被顛覆,而隨著社交網(wǎng)絡、協(xié)作化內容社區(qū)的探索,人類通過網(wǎng)絡構造的新的知識圖譜,獲取新的內容的方式正在深刻變革。也許你并沒有注意到,用歷史觀來看人類知識圖景的變遷,確實值得反思。
來源:鈦媒體
作者:Lonelist
“讓人類所有的知識百川匯海”——這個夢想如啟明星一樣照耀在維基百科十三年的歷史之上,使之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大規(guī)模知識協(xié)作的一個“奇跡”。然而,在存量知識已經(jīng)漸漸“顆粒歸倉”,而增量知識又因為支離破碎而無法撿拾,在時間線上隨著不斷的刷新朝生暮死,維基百科正在離成立之初的雄心壯志越來越遠。
曾經(jīng)以“大英百科”革命者的角色沖上“互聯(lián)網(wǎng)風口“的維基百科,如今正在成為“被革命”的對象。當信息呼嘯而來的速度緣遠超過了人們處理、歸檔的速度,“匯聚人類所有知識”將成為一種圖書館時代的田園牧歌,或者說一場注定失落的夢。
維基百科的危機
《The decline of wikipedia》、《維基百科,前路何在?》《維基百科過時了嗎?》......自2012年以來,對于維基百科的唱衰之聲如野草般在網(wǎng)絡上潛滋暗長。從MIT Technology Review、《The economist》到國內的《南方周末》、果殼網(wǎng),維基百科的遲暮景象被放在顯微鏡下逐一探討。而關于維基百科遭遇的危機,可以概括如下:
- 編輯隊伍萎縮:英文版編輯在過去年下降了三分之一。
- 在移動端毫無建樹:只有1%的內容通過移動端編輯。
- 官僚主義愈演愈烈:在維基中,流行的是“被管理員欺負的故事”以及“反抗管理員的故事”。
- 激勵機制失去吸引力:Facebook、Twitter、Snapchat……層出不窮的移動應用正在奪去人們的時間和關注。
理想主義的光環(huán)總是容易遮蔽人們的眼睛,在進入互聯(lián)網(wǎng)編年史之前,維基百科先要被媒體的“祛魅”扒一層皮么?
“維基百科在2001年是完全合乎時宜的,但從那以后就開始過時了。”或許只有當局者看得最清,維基百科委員會蘇加德納欲言又止的話值得深思。
回顧維基時代,依然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事情。2001年維基百科橫空出世時,熱情歡呼的人群只注意到了它身上散發(fā)出的青春荷爾蒙般的反叛氣息。人人都可以編輯的百科全書,將正襟危坐在人類知識頂端的那一群老頭子(例如大英百科編輯委員會)踢下去,發(fā)動“無組織”的組織力量,讓知識的汩汩細流通過千萬道互聯(lián)互通的光纜匯于一處,免費供任何人隨時隨地“取一瓢飲”。
2001年,互聯(lián)網(wǎng)還是一片蒼涼荒蕪的知識荒原,人類歷史上90%以上的知識游離在互聯(lián)網(wǎng)之外,被囚禁于封面、封底之間,散落于大地四方。那時候,剛成立兩年剛站穩(wěn)腳跟的Google還來不及發(fā)布其野心昭然的“Google 圖書計劃”;而亞馬遜還沒有從“高臺跳水“的余悸中緩過神來,為了用盈利證明自己而全力沖刺,無暇他顧;已經(jīng)緩慢推進30年的古登堡計劃尚未積累1萬本數(shù)字圖書。而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則在人們舉目眺望的地平線之外。
這個時候維基百科的“振臂一呼,云集響應”就不難理解了。互聯(lián)網(wǎng)早期的網(wǎng)民都被一種“拓荒者”的激情所裹挾,能夠為互聯(lián)網(wǎng)的知識大廈添磚加瓦,在這座“亞歷山大圖書館”中留下自己的名字,該是一件多么激動人心的事。維基百科的志愿者們心甘情愿做“知識搬運工”,人肉掃描儀,義務網(wǎng)絡編輯,當然還有“知識的仲裁者”——去偽存真——信息的過濾者。
然而,這群從互聯(lián)網(wǎng)的各個角落發(fā)起沖鋒的志愿者,雖然成功地將專家學者們趕下神壇,卻在做著與他們相似的事情。
實際上,創(chuàng)始人威爾士遠沒有媒體報道的那樣渾身逆鱗,他不得不一次次扯掉外界給他披上的“戰(zhàn)袍”。他從來不承認維基百科是“自下而上”、無政府主義的,他延續(xù)了“條目”這種信息組織方式,他以“中立主義”為維基百科的生命線,追求言必有據(jù)——正是這些從舊時代繼承過來的傳統(tǒng)理念塑造了維基百科的形態(tài)。
而這些理念顯然會與“人人都可編輯”的理想難以兼容。
民主的困境
如果你想知道世紀初的網(wǎng)站長什么樣子,看看維基百科就好了。它就像是一個“江流石不轉”的時間膠囊,自誕生到現(xiàn)在幾乎沒有變換容顏。正如魯迅所說的“在中國搬動一張桌子就會導致流血事件”,100萬編輯過詞條的維基人都把自己視為維基百科的“主人”。網(wǎng)站一絲一毫的變動都要經(jīng)過曠日持久的討論和爭辯,就連威爾士本人也沒有權利拍板下決定。
2007年以來,為了應對維基百科的內憂外患,維基委員會做出了各種改進的努力:例如推出可視化編輯器,模仿Facebook引入“點贊”按鈕等,然而推進起來舉步維艱。
Quora上wikipedia標簽下有一個熱門問題:維基百科糟糕的用戶界面為何不見一點改進?
維基基金設計師Brandon Harris的回答是:
我們一直在努力,但收效甚微,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不是私人公司。Facebook可以頂著用戶山呼海嘯的反對聲浪對網(wǎng)站“動手術“,而我們不能。(其他原因包括:薪酬無法吸引頂尖程序員,只能盡量雇傭志愿者;370種語言,覆蓋全球的網(wǎng)絡架構牽一發(fā)而動全身,“This is an enomous task。”)
2010年中文維基首頁改版時候,就曾有互聯(lián)網(wǎng)人士發(fā)起討論“設計的民主和獨裁問題”。
“人人皆可編輯”之不可能
開放、人人平等、去中心化——這些被寫進《維基經(jīng)濟學》、《眾包》,被視為維基百科“成功密碼”的理念在成立幾年之后開始黯淡失色,為了保證條目的“客觀中立”不得不被迫讓步、犧牲。
任何一個開放系統(tǒng)都難以避免混亂、錯訛、破壞者的闖入,枝蔓橫生,但是以大英百科為榜樣的維基百科卻無法容忍這些,需要在第一時間將雜草刈除干凈,有無數(shù)雙挑剔的眼睛在拿著放大鏡緊盯這個闖進知識界的“野蠻人”,每一處差錯都會變成唱衰者手中的武器。
對偽造、惡作劇、造謠中傷、夾帶私貨等信息的生殺予奪造就了維基百科的權力階層——管理員小組,圍繞著對評判標準的爭論,管理層內部又不斷分化裂變,出現(xiàn)了“刪除主義維基人協(xié)會”及針鋒相對的“收錄主義維基人協(xié)會”,還有“不主張對條目價值做出一般性判斷,贊成刪除某些特別糟糕的條目但不代表我們屬于刪除主義的維基人協(xié)會”。
各個派別會在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地方爭論不休,寸步不讓,維基百科著名的“編輯戰(zhàn)“由此得名。2006年底,關于該把養(yǎng)貓的人叫做貓的“主人”、“照料者”,還是“人類伴侶”,“貓”這一條目的編輯們爭執(zhí)不下。三周后,他們展開的長篇討論足夠裝滿一本書。
權力階層除了意味著圍繞“編輯器”的爭奪戰(zhàn),還意味著普通維基人的不平等和對新人的排斥。為了打擊惡意編輯行為,管理層推出了一系列編輯工具和繁瑣復雜的標準規(guī)范,還啟動了可以“一鍵刪除”可疑條目的“機器人”,初來乍到錯誤難免的新人一盆盆冷水迎面而來,辛辛苦苦編輯的條目轉眼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卻往往申辯無門。
有人建議維基百科應該更新它的格言:不再是“任何人都能編輯的百科全書”,而是“任何理解標準規(guī)范、善于社交、能繞開冷冰冰的半自動化駁回城墻而仍想要自愿貢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的人都能夠編輯的百科全書。”英文版維基百科的活躍編輯數(shù)量在2007年一度達到5.1萬以上的峰值,隨后由于新人青黃不接,這個數(shù)字一路下滑。到去年夏天,只剩下了3.1萬。
維基百科的管理員們當然不是故意要和新人過不去,他們只不過是一支無力一一排查千萬詞條只能“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糾察隊。長達5000字的編輯規(guī)范、層層設障的提交程序,以及成為很多潛在維基人面前“攔路虎“的wikitext編輯器,都不過是為了提高“搗亂者“的成本而已。
“人人皆可編輯”——維基百科的這塊基石已經(jīng)搖搖欲墜了。
“中立主義”吃力不討好
而“中立主義”也正在成為束縛維基百科自由生長的一個囚籠。
如果說大英百科的“客觀中立”依靠業(yè)內專家的一致意見來實現(xiàn),那么對于維基百科來說,“當一個條目的內容趨于穩(wěn)定,各方意見的爭鋒塵埃落定時,我們可以說它達到了中立狀態(tài)。”(威爾士語)
“我們贊同公平地表現(xiàn)每一個重要的觀點,且不去斷言哪一觀點是正確的。這便是在此種意義下讓一篇條目‘無偏見’或‘中立’的秘訣。“維基百科“中立觀點”條目給出了關于“中立”如何實現(xiàn)的官方說法。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許多人理想中的“擱置爭議,相安無事,共同呈現(xiàn)。
“完全基于內容本身所表現(xiàn)的觀點,而將文字或內容‘隔離’到不同位置或子章節(jié)的作法,可能導致非百科性的條目結構……更加中立的做法應該是將爭議寫入敘述性的內容中,而不是將它們提煉成單獨的章節(jié),無視對方的存在。”
紛蕓多歧的觀點“統(tǒng)一于”單一的文本中,這就是維基百科之所以叫做“百科”而不是“觀點PK臺”的原因。這也是硝煙彌漫的“編輯戰(zhàn)”的一根導火索——各方都想盡量把自己的“私貨”塞到正文中。
雖然威爾士希望各方觀點能夠通過理性溝通協(xié)商,達成共識,最后根據(jù)其在“可靠來源“中的流行程度確定各自在條目中所占比重,但往往事與愿違,凡是熱門的條目都布滿了煙硝和彈痕。
陸港臺三地青年共同參與的中文維基百科可謂是“編輯戰(zhàn)”極端化的一個縮影。“兩岸歷史和現(xiàn)實的復雜性讓爭論變得頻繁而瑣碎,就連一個方框都能成為戰(zhàn)場。中文維基要編一個中國朝代年表,但到1949年后,臺灣維基人要求臺灣并列在大陸旁邊,而且表格大小要一樣。大陸維基人則表示反對,認為應按兩岸實際面積大小來劃分。“解放戰(zhàn)爭”、“第二次國共內戰(zhàn)”、“平型關戰(zhàn)役”等條目都成為一場場拉鋸戰(zhàn)的中心。戰(zhàn)火從單個條目演變?yōu)椤傲T免管理員”的治理危機,沸沸揚揚到讓威爾士一度動過關閉中文維基的念頭。
“編輯戰(zhàn)雙方如果長期無法形成共識,造成‘封了就停,解了就打’的尷尬局面,怎么辦?”這不僅僅是中文維基面臨的問題。
在大英百科時代,學界就某個詞條該怎么寫達成共識并不是件難事。因為知識高度集中于一小撮專家學者手中,只要他們坐下來吃吃茶、談談天,各讓一步,大不了由委員會一錘定音。什么,不滿意?等下一次修訂再說吧。而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茶杯里的風暴”變成了“人民戰(zhàn)爭”,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一千條論據(jù)來支撐自己的觀點,隨著新信息的不斷涌現(xiàn),“偏見守衛(wèi)戰(zhàn)”將永遠沒有結束的那一天。“Filter bubble“更是會把人們困在一個個彼此隔離的“氣泡”內,讓偏見得到更多瘋狂生長的養(yǎng)料,讓人們只看到口味相符的信息,只需和氣味相投的人廝混在一起。
四平八穩(wěn)、各方都不討好的“中立主義”已經(jīng)隨著傳統(tǒng)媒體的沒落走向窮途末路,維基百科的“中立主義”理想的吸引力還能持續(xù)多久?
關于維基百科最著名的隱喻就是數(shù)字時代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浩瀚恢宏、一眼望去不見盡頭,維基百科的一切設計都圍繞著這個終極目標。在這里,人人都只是搬運工和泥瓦匠,人們的名字都隱沒于這項工程的熠熠光輝中而渺小不可見。雖然維基人的數(shù)量達到了千百萬級,但這卻是一張“蟻群“一般的匿名社群,從中延伸不出來社交關系網(wǎng)——因為這里不是以人為中心,而是以條目為中心。
這就讓維基百科無法順利地轉型成為一個類似于Facebook那樣的高黏性社交網(wǎng)站,當互聯(lián)網(wǎng)“拓荒時期“的理想主義不再有鼓蕩人心的感召力,當“there isn't a lot of low-hanging fruit“,編輯門檻越來越高之后,如何激勵更多的用戶參與進來?
克萊舍基曾經(jīng)在《人人時代》中對維基百科陌生人之間的協(xié)作力量不吝贊美,但是現(xiàn)在他不得不承認:時代變了。如今的人們更關注與維護以自我為中心的信息流,從點贊、互動中獲得持續(xù)不斷的瞬時激勵。
后維基時代的知識圖景
讓我們來看一下后維基時代的知識圖景是什么樣子的吧。
1、圍繞人而產生。維基百科延續(xù)了傳統(tǒng)的知識生產方式,將知識從人們的生活中抽象、抽離出來,分門別類地歸置于一檔檔“文件夾”中,供人取用。在社交網(wǎng)絡及移動互聯(lián)時代,知識隨時隨地圍繞著人而產生,不能脫離生產者而獨立出來。“誰說的”有時候比“說什么”更為重要。
2、碎片化而非結構化。知識的結構化是古登堡時代的產物,當書籍這種知識組織方式已經(jīng)隨紙張一起走入故紙堆時,維基百科將所有相關內容都收納于一個個“條目”的做法也就隨之out了。(君不見維基百科的條目有越來越長的趨勢,很多條目已經(jīng)長成了一本書的樣子。)碎片化信息并不代表著沒有價值,只是等待用大數(shù)據(jù)的方式聚合、整理、分析、使用,也會在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頭腦中凝聚、提煉為可供使用的“知識”。如果說過去的結構化知識是少數(shù)人為所有人調配好的“知識菜譜”,那么,現(xiàn)在,每個人都可以利用“碎片化”的原料烹飪出自己的“知識大餐”。
3、多種形式而非僅僅只是文字、圖表。維基百科的公益性決定了它注定沒有能力在條目中插入音頻、視頻、信息可視化等多媒體內容。離開了這些,它還如何能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匯集了人類所有的知識呢”?
4、不再追求標準答案。正如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一樣,知識不再是可以打開所有鎖的“萬能鑰匙”。想在一個條目中歸納出一個問題的“標準答案“成為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比如對于自由主義、福利社會這些左右派火力交鋒的“焦點”,怎么可能寫出一個讓所有人滿意的“標準答案”呢?這也難怪維基百科的自然科學條目的質量明顯高于政治、經(jīng)濟等社會科學條目。
我們當然不是否定維基百科的價值,就像大多數(shù)人都會承認的那樣——它仍是我們所能擁有的最好的百科全書。只是“百科全書”這種沉重的形式已經(jīng)無法在互聯(lián)網(wǎng)浪潮中繼續(xù)溯流而下了,而是慢慢沉降、觸底,不再前行。
在互聯(lián)網(wǎng)誕生至今的二十多年間,有無數(shù)url已經(jīng)成了永久的“死鏈”,比特海中沉入最深處無法打撈的遺跡,維基百科上早期的很多鏈接就指向這些“知識的黑洞”。多虧了維基百科為我們保存了2001年至今的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檔案,互聯(lián)網(wǎng)知識庫增長路線圖(雖然形式萬年不變,但是每個條目的每一次編輯記錄卻都被保留了下來。)
我們不能肯定維基百科是否能一直存在下去,但是起碼到今天為止,維基百科已經(jīng)成為網(wǎng)絡時代的“日用品“,互聯(lián)網(wǎng)底層的“基礎設施”,將“公認”的知識變成計算器上“=”鍵那樣觸手可及的東西。
而維基百科壯志未酬的事業(yè)則有待后來者接過大旗繼續(xù)走下去。
如何將散落在各個“圍墻花園”中的知識碎片歸攏起來,再圍繞人們隨時隨地的需求聚合起來,為人所用?如何避免信息隨timeline的刷新不斷被覆蓋、埋葬,消失不見的命運?如何激勵人們將個人知識分享出?如何讓“知識眾包”躍過社交時代的龍門,進化得更有效率、更有吸引力?
算法編織的知識圖譜
一前一后誕生于世紀之交,Google和維基百科曾是一對相生相促的好“基友”。Google用Pagerank算法讓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浩瀚信息“排排站”,隨時隨地供人調遣使用;而維基則則通過“螞蟻雄兵”將互聯(lián)網(wǎng)的link機制運用到極致,編織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張縱橫交錯的知識網(wǎng)。維基百科的條目常常會出現(xiàn)在Google搜索結果的第一頁上,Google也是維基百科的贊助人之一。
但是,隨著“信息煙塵”越來越遮天蔽日,丟給用戶一大堆密密麻麻的鏈接的做法已經(jīng)無法讓搜索者滿意,他們需要一個現(xiàn)成的答案,Siri、Facebook等競爭者的出現(xiàn)加深了Google的危機感。Google Konwledge Graph于2012年5月正式發(fā)布,它會用“語義網(wǎng)”將用戶搜索關鍵詞這一點周圍的“知識譜圖”展現(xiàn)出來,使用戶一步到位地獲取想知道的所有相關知識。Konwledge graph被認為下一代搜索引擎的核心——提供的是答案,而不僅僅是鏈接。在Google Konwledge Graph這張網(wǎng)絡上,維基百科只是數(shù)據(jù)來源之一。相比于維基百科在單一站點內人工編織的知識網(wǎng)絡,Knowledge Graph是一張更為恢弘壯麗的覆蓋整個互聯(lián)網(wǎng)的知識“全景圖”。
在維基百科這項“底層設施”之上,Google正在做超越維基百科的事情。維基百科是面向所有人的百科,而Google Knowledge Graph則會在每個人面前展現(xiàn)出獨一無二的知識圖譜。
然而,互聯(lián)網(wǎng)上正在誕生一個個將Google爬蟲拒之門外的“圍墻花園”,F(xiàn)acebook就是最大的一個。不僅如此,F(xiàn)acebook還正在通過把“l(fā)ike”、“send”按鈕安插到互聯(lián)網(wǎng)各個角落的做法,試圖顛覆Pagerank的游戲規(guī)則,從而動搖Google帝國的根基。
正如我們在前文提到的,后維基時代,知識圍繞著人而產生,F(xiàn)acebook的“l(fā)ike”、“send”按鈕就是人們對網(wǎng)頁、人、地點、事物的一次次投票(當然,好友的投票會有更高的權重),直接決定了知識的重要程度和與用戶關系的遠近,、這比Pagerank把網(wǎng)頁按照鏈接數(shù)量的多少排序這種“冷冰冰”的做法User frendly多了。
扎克伯格把2013年初推出的Graph search稱之為“第一個巨大的產品”,雖然他聲稱該產品并非劍指Google,但明眼人一看便知Graph search絕不甘心只做一個Facebook站內的社交搜索,而是要用社交關系鏈重新構建互聯(lián)網(wǎng)的知識圖譜,為信息增加“人”的維度。Facebook在自己10億用戶的“地盤”上可以自己說了算,但是開放平臺覆蓋的范圍顯然還難以企及Google爬蟲掃過的土地。扎克伯格深知“萬里長征才走了第一步”,5月6日在接受《連線》采訪時,他說“Graph Search還處在初期階段,甚至都還沒推出移動版,而大多數(shù)用戶都會通過移動端使用我們的產品。”
“在Facebook網(wǎng)站上發(fā)布的帖子中,有5%到10%是人們向其好友提出五花八門的問題,如‘這段旅程中下一步我該去哪兒’或者‘誰該做我樂隊的鼓手’,諸如此類。而在傳統(tǒng)的搜索引擎中,你是不會問這樣的問題的,但存在于我們的體系中的知識很可能將給你帶來指路明燈。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那么就能改變人們對社交網(wǎng)絡的看法,也就是社交網(wǎng)絡不僅僅是與通信有關而已,還能帶來知識和解答問題。”在扎克伯格眼里,F(xiàn)acebook顯然不只有自拍照片、流言八卦而已,它也將成為社交網(wǎng)絡一代的知識來源。
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和傳統(tǒng)互聯(lián)網(wǎng)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網(wǎng)頁靠邊,應用當?shù)?在那里,圖片、視頻、位置、健康狀況等個人化的信息每時每刻都在被創(chuàng)造出來,分散于數(shù)十萬個封閉的應用中,令Google等搜索引擎難以染指。而Facebook的send、like按鈕則可以輕而易舉地接入應用之中,從而共享其中的海量數(shù)據(jù)。(至于Google+,F(xiàn)acebook的Party都已經(jīng)開始了,誰還想挪地兒呢?)
無論是Google還是Facebook,關心的顯然都不是“人類知識向何處去”,而是如何推送出更精準直達的廣告。正如有些人哀嘆的“我們這一代最聰明的人竟然都在思考著怎樣讓人們去大量地點擊廣告”,似乎與維基百科的志愿者們有云泥之別,但是Google、Facebook卻在無心之中繼續(xù)著維基百科未競的事業(yè),而且走的更遠。
“后維基時代”的知識協(xié)作
然而,短時期內,Google、Facebook算法所依靠的語義網(wǎng)還無法像維基志愿者一樣在不同的信息之間建立準確的鏈接,也就是說,人類在分類、歸納、聯(lián)系等方面復雜幽微的思維能力機器還只學會了皮毛而已。碎片化的知識已經(jīng)在如雪崩一般轟炸而來,我們手中卻還沒有可以馴服它們的武器,只能不斷提高大腦這個“信息處理器”的運轉速度,連和菜頭這樣的“資深網(wǎng)蟲”都感到“力倦神疲”,落荒而逃了。
從博客時代開始,各家社交網(wǎng)絡不約而同地采用了以“時間線”倒序、實時更新的信息組織方式,讓信息如過眼煙云般前赴后繼,除了滿足即時的消費需求,很難沉底下來。之所以如此,不過是因為“時間線”不需要人工的干預,不需要復雜的算法而已。
Quora這樣問答網(wǎng)站就是為那些Google不到結果、在維基百科上查詢不到的問題的問題尋找答案。這里就像是一個知識市集,各行各業(yè)的人交換著經(jīng)驗、知識和看法。一個問題就是一群知識的集合,答案按照得票多少而非時間先后呈現(xiàn)。在暖暖的燈光下,流傳著勵志故事、公司內幕、行業(yè)觀察、親身科普……這里沒有標準答案,有的是圍繞某個問題的智力風暴,呈現(xiàn)的是一件事情的多個面向而不是“標準照”。
在問題之外,Quora也在嘗試著用“領域”、“話題”、tag的方式將分散在各個問題中的知識組織起來。與此同時,因為回答問題而成為某一領域專家的用戶也會成為一個個知識的“節(jié)點”,一本本“活的”行業(yè)百科。有人曾經(jīng)吐槽維基百科“最熱情,最能耗,最有時間的用戶貢獻/維護了最多的詞條,而不是最有專業(yè)知識的。”與此相比,問答網(wǎng)站上的專家則要貨真價實的多,絕不僅僅是精力旺盛的“搬運工”,比如關于量子力學的問題會有大學物理教授來回答,而關于Google的問題則會有內部員工來“爆料”,這些非標準化的知識是維基百科所無法提供的。
與維基百科相比,問答網(wǎng)站的社交屬性更強,每一個認真的回答都會收獲一個個“贊同”,增加回答者的聲望,從而產生比“理想主義”更為有效的激勵作用。用戶之間的互動交流不僅有助于問題持續(xù)深入的討論,形成的社區(qū)氛圍也會讓更多志趣相投的人留下來。
曾經(jīng)一手創(chuàng)立了Blogger、Twitter的Evan Williams希望借Medium打破“時間線”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它更像是《赫芬頓郵報》和Blogger的進化版,用主題為核心的內容組織方式來聚合內容、用用戶投票的眾包形式進一步精選內容、用精美的網(wǎng)站模版來加強頁面的結構化。
Medium就像是對這個社交為王、碎片紛飛的時代殺出的一記“回馬槍”,一次反動逆。這里甚至不鼓勵讀者評論,讀者有話想說可以在作者的文章中添加批注——Medium的協(xié)作性正是體現(xiàn)在這里。《喬布斯傳》的作者艾薩克森 艾薩克森已經(jīng)在上面寫作一本關于60年代計算機文化的書,他希望借眾人之力使這本書更為豐富、準確。
而最近低調上線的寫作者社區(qū)“十五言”——這個Medium的“像素級”山寨者則有著更為ambitious的愿景。
果殼網(wǎng)的創(chuàng)始人姬十三在《用十五言完成系統(tǒng)知識的眾包》的文章中中寫道:“前幾年曾想過做一個產品,用眾包來完成知識地圖的系統(tǒng)化整理。各種原因擱淺了。維基百科當然也可以完成類似工作,但維基淡化個人品牌和風格,整體注重嚴謹卻可讀性不強。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伙人,甚至是一伙沒有協(xié)作經(jīng)驗的人,在優(yōu)秀的產品機制組織下,快速完成一定份量的內容,既能讓讀者對這個領域的知識有全貌了解(系統(tǒng)化整理),又有一定可讀性,相當于一起出一本書。”
不過,從代碼原封不動照抄Medium這點來看,姬十三可能只是說說而已,并不打算當真。
知識協(xié)作的價值何在?也許這些后來的實踐者將逐漸揭曉答案。
本文系作者授權數(shù)英發(fā)表,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數(shù)英立場。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載侵權必究。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載侵權必究。
本文系作者授權數(shù)英發(fā)表,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數(shù)英立場。
未經(jīng)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未經(jīng)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數(shù)英立場。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本文系數(shù)英原創(chuàng),未經(jīng)允許不得轉載。
授權事宜請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授權事宜請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暫無評論哦,快來評論一下吧!
全部評論(0條)